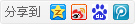京滬天地(三)
在武漢停留10天以后——毛澤東在這里對當地形勢作了考察——這一行人到達北京,正好參加在湘鄉會館舉行的有千余人參加的反張集會。毛澤東帶著一條標語來到會場:“張毒不除,湖南無望。”
毛澤東在古老破敗的福佑寺租住下來,這里位于故宮附近的北長街。他睡在沒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鍍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間閱讀和寫作的地方是一條香案,油燈搖曳的火苗將其映成怪影。香案旁邊是一臺油印機——這是新時代從事政治活動的圣物。這里就是這位來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稱為“平民通訊社”的印刷車間。

毛澤東的驅張計劃并沒有多大進展。北京的世界更廣闊,所關心的是更大的問題:大軍閥統治的“國民”政府的腐敗;凡爾賽會議以后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反響;五四思想的傳播。毛澤東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顧的眼神。
毛澤東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獲是楊小姐。楊開慧比毛澤東小八歲,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少女,圓臉龐,皮膚白皙。毛澤東在前一次來北京時,就已萌發對她的愛情,現在他們的感情更深了。
毛澤東到達北京一個月之后,楊教授去世,這似乎為毛澤東與楊開慧的結合開辟了道路。
這對情侶開始了他們的“試婚”,這是楊教授不曾贊成的,不過他們在北京并沒有共同的居處。他們在毛澤東棲身的北長街寺里的神像旁見面,或者去溫暖舒適的楊家。春天,他們一起到西山騎馬漫游,在僻靜處相會。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過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楊的結合是自由戀愛的結晶,這在舊中國是極為少見的。一年以后在長沙舉行的結婚儀式只不過是走過場而已,很少有人記在心中,甚至毛澤東本人在1936 年與埃德加· 斯諾談話時,也回憶不起這次婚禮的確切日子。
長沙的趙女士沒能活著去光揚五四道德準則,而楊小姐的奮爭使這種精神在政治運動中得以體現。死去的趙女士使毛澤東滿腔憤懣盡訴筆端,活著的楊小姐則令他心醉神迷。趙女士永離人間。楊開慧則在精神上給毛澤東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澤東在20 年代進行筆戰和繼之以真槍實彈的斗爭。
也是在那寺廟的香案上,毛澤東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他熱心搜讀各種譯成中文的有關材料)。這一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動了他。部分是因為《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譯本在中國1919年11月出現——是當時在中國最有影響的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為俄國革命后,經過李大釗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輝。
蘇俄成了毛澤東的指路燈塔,就像1790年法國之于英國的激進派一樣。他對馬克思理論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婦女的交談中表現出他對新俄羅斯的熱情。那位婦女說:“搞共產,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腦殼。”毛澤東激動地回答:“腦殼落地,砍腦殼,當然,當然,但是你要曉得共產主義多么好!那時國家不再干涉我們了,你們婦女自由了,婚姻問題也不再拖連你們了。”
對毛澤東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思想,它解釋歷史是怎樣從一個階段演進到下一個階段。
毛澤東對于革命行將帶來的社會前景考慮不多。他也沒有注意到最為艱難的關鍵問題是要奪取政權。不過,在1920年他已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認為中國的命運要與俄國式的革命連在一起。
只有這樣才能拯救國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釋放,五四英雄們的理想才能在社會中實現。
馬克思主義絕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種疾病那樣,只是從一種歷史環境傳播到另一種歷史環境,而是在新的環境中再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也正是這樣。自1919年他成為《新青年》的讀者時,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已在心中播種。圣彼得堡傳來的消息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的吸收僅是毛澤東的思想演進的第三個階段。
“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毛澤東談起他在北京度過的第二個冬天,“使我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除《共產黨宣言》外,還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后兩本書給予毛澤東的不是很純的馬克思主義。
不過,毛澤東已經確立了自己的“信仰”。從1920年夏天開始,他認為自己已經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并且以后從未動搖過。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和空想主義都從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擠出去了。
毛澤東并沒有在一夜之間吞食馬克思、脫胎換骨變成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從他繼續從事湖南自治運動的行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離開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這里并不能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楊開慧自父親死后便隨母親一起回到長沙。毛澤東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時間與她相聚。
在那個時候,他還希望與陳獨秀教授詳論自己新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變賣了自己過冬的大衣買了火車票起程去上海,腦子里裝著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澤東處境艱難,他為大班和富有的買辦洗燙衣服并要來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當伙計,每月的薪水是12塊至15塊錢。其中約要八塊錢用作車費,因為他要往來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間。如果說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對上海很少露出笑臉的話,我們不難理解個中緣由。
毛澤東期望陳獨秀在湖南問題上予以指導,但這位革命的教授手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產國際派遣的俄國顧問已經到達中國,與李大釗和陳獨秀商討關于在中國成立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具體事宜。
那年春天,陳獨秀是迄今所知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最大的人。
“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后來談起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傳統斗士時說。毫無疑問,洗衣店的艱辛使毛澤東進一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幫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所說的“無產者”這個詞的意義何在。

1920年5月8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
毛澤東去碼頭向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送行,陽光閃爍在黃波蕩漾的黃浦江面上,潮濕的空氣中回蕩著裝卸船貨的號子和汽笛聲。毛澤東身上穿著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長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學會會員在上海的半淞園舉行了會議。毛澤東講了話,他提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口號。會議決定委派 他回長沙任湖南勤工儉學運動的負責人。大家鄭重地合影后,便沿著吳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國貨船。
有些女生隨這伙人一起出發了。讓女生參加這一運動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貢獻。他曾對領著一幫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說:“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他對婦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體現了他對舊中國的憎恨。
有位學生對毛澤東沒有赴法表示遺憾,毛澤東回答道: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們歸來再著手。”
毛澤東獨自站在斜坡上,看著朋友們依次走進船尾的四等艙。在他轉身走回市內前,他高聲喊道:“努力學習,拯救國家。”
湖南的內戰連續不斷。但是到了1920年夏,戰爭以張敬堯敗走和較為開明的譚延問上臺而結束。毛澤東在這種新的自由氣氛下帶著滿腹政治計劃回到長沙。
奉譚之命擔任騷亂不已的第一師范校長的人恰巧是毛澤東過去的老師,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澤東為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修業學校的主事。主編《湘江評論》時,他曾在修業學校教過課。當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國做工時,毛澤東無可爭議地成為新民學會的領導人。
修業小學的報酬豐厚,主事的職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澤東很快就顯示出他不只有儉樸的一面。他與楊開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這是一個財主建在花園中的住宅,寧靜而雅致。租金每月12 塊,與他在上海洗衣店時的收入一樣多,超過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收入的50%。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已躋身長沙上層社會。
1920 年至 1921 年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趨于一致的時期,這給他的政治生活帶來新的目標,也給他的親屬多少帶來一些痛苦。
毛澤東把五四精神推向前進。他創辦了青年圖書館,又(與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學生聯合會。在回韶山的幾周內,他給家鄉傳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一個教育促進會。他在湖南《通俗報》上撰文并擔任編輯。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報紙,毛澤東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編后,該報便轉向左派。
在一位與他關系頗好的女同學——她也是楊教授最好的學生之一——的幫助下,毛澤東創辦了文化書社,在湖南傳播左翼文化的種子。“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他在《文化書社緣起》中寫道。
毛澤東在湘雅醫學專科學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間房作文化書社社址,并從楊開慧的母親那里得到經濟上的資助。他甚至請擅長書法的軍閥譚延閩為書社寫招牌,出席開業儀式。在那個下午的開業典禮上,這兩個冤家對頭握手言歡。
書社營業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鎮成立了七個分社。初期最暢銷的書籍有(都是中文書刊) 《社會主義史》、《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新俄國之研究》等,雜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勞動界》 。
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主旨中增進了親蘇俄的內容。他和《通俗報》主編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并發起了赴俄勤工儉學運動。在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影響下,毛澤東試圖組織勞工聯合會。在共產國際的建議下——這些建議從北京和上海通過信件傳給他——他開始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同時他還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一共產黨外圍組織。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廳辭退,《通俗報》的激進分子也一齊被解雇。毛澤東聘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修業小學的教師。在反抗斗爭中,如果說學生是中堅力量,那么小學教師則像一根紅線把他們與那影響不斷擴大的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行營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