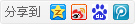京滬天地(二)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200 萬人)已成為西方的門戶,商業貿易是其血脈。毛澤東不喜歡待在上海,因為這里沒有古跡、勝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丟拜見通過《新青年》結識的他的第二個楷模陳獨秀教授,這位研究文學的學者1917年迫于軍閥的壓力從北京搬到了上海。這次會面為日后的進一步接觸播下了種子,盡管這個第一次會面還沒有到火候。

毛澤東在上海漫步街頭,閱讀報紙,拜訪湖南友人。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長沙的事務上。有一樁好事來了,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撥給他一筆錢,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 年 4 月,毛澤東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車船回到了長沙。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反帝愛國運動。這是北京大學學生的示威游行隊伍。
當時毛澤東的境況非常艱難。他在湖南大學為投考者而設的學生宿舍里找到一張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師范的附屬小學兼些歷史課的教學。毛澤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確實沒法從事固定的工作。
毛澤東過著清貧的物質生活,盡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雙大腳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實用:吃的飯食主要是蠶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經常要依賴別人。
北國之行明顯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記。在北京時他沉默寡言,在長沙他有很多話要說。他的第一次冒險舉動是公開地講馬克思主義這一新奇思想,雖然對此他只知一點,也只這么一點。
1919年下半年,毛澤東成為長沙地區新文化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兩個主題。當時的主要矛頭指向湖南軍閥統治者張敬堯,這位半封建式的親日派曾使五四學生付出了血的代價。
毛澤東領導了長沙的五四運動,使運動主旨的兩個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驕陽似火的6月,他在長沙組建了“湖南學生聯合會”。
學生運動的熱情空前高漲,這在全國首屈一指,即使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騷亂較之也略遜一籌。學校有半數時間停課(理想的“真理”壓倒了現實)。一紙宣言可以引起學生第二天更大規模的游行。包里裝著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著雨傘,學生們走出長沙與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聯系。幾乎每個人與自己的家庭都發生沖突。印刷粗糙的小型雜志不斷涌現,標題都帶著一股高昂的情緒:
《覺悟》、《女界鐘》、《新文化》、《熱潮》、《向上》、《奮爭》、《新聲》 。
以20世紀60年代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學生絕不摩登。他們中的大多數是身穿長袍馬褂的紳士,慣于對仆人指手畫腳。他們一只腳站在傳統的門檻里面,嘴上卻言辭激烈地反對傳統。與美國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樣,他們和周圍人一樣生活,但嘴上卻說是周圍的人污染了他們純潔的心靈。
有一個大學生剁掉自己的兩個手指以抗議督軍張敬堯的殘暴行徑。13歲的丁玲(她后來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帶領全班同學沖進湖南省議會的議事廳,要求婦女有財產繼承的權利。年齡越小,他們越無所顧忌。
毛澤東在一個“使用國貨,抵制日貨”的集會上發表演講,而沒有注意到中國產品還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這一事實。他組織一批女學生——從一開始他就把女學生吸收進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核心——在長沙街頭檢查店鋪,警告老板要銷毀日貨。毛澤東后來回憶說:
“當時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事實的確如此,晚間政治活動之后一兩個小時的休息,不帶邪念的男女相依而臥不會發生情事。毛澤東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聰明美麗的妹妹蔡暢曾立下三人盟約:發誓永不結婚。但是他們三人都違背了這一誓言,毛澤東則違背了三次。
這不表明他們的誓言是戲言,而是表明他們一度曾經具有的思想——像美國福音信徒——他們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們認為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但愛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為他們的事業增添光彩。
學生的社會處境使他們處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們是蒙恥受辱的一代。古老傳統的粉碎使他們根基頓失,國家的風雨飄搖又使他們瀕臨絕望。
做舊中國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膽量來付諸行動。對外表堂皇、內部腐敗的舊中國的公然反叛,猶如揮戈猛刺一個外皮尚好、里面爛如狗屎的西瓜,民眾會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爛透的西瓜又始發青春。在1919年的中國喚起民眾的反抗并非難事。在那個暴風驟雨的夏天,毛澤東為學生聯合會而奔走忙碌,他創辦了一份周刊,自任編輯和主筆,并依地名將該刊物命名為《湘江評論》。第一期《湘江評論》印了2000份,一天之內就銷售一空。以后每期印5000份 (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該雜志鋒芒犀利,充分表達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話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語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穌的原話改寫欽譯圣經一般的驚人。
的確,甚至胡適教授也認為毛澤東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紅格薄紙上草就的文章筆鋒銳利。生動活潑,對每一個論點都表述得很詳細。他以前如饑似渴地讀報紙終見成效。
“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毛澤東作為編者在發刊詞中宣稱。“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顯示了他當時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在中國的一份報紙上,我們看到當時的一位小學教師對毛澤東的回憶,文中不乏溢美之辭,但很有史料價值。
《湘江評論》只編寫5期,每期絕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幾天。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只好自己動筆趕寫。他日間事情既多,來找他談問題的人也是此來彼去,寫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氣的熏蒸,不顧蚊子的叮擾,揮汗疾書,夜半還不得休息。他在修業小學住的一間小樓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著一層板壁。我深夜睡醒時,從壁縫中看見他的房里燈光熒熒,知道他還在那兒趕寫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寫好了,他又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自己到街上去叫賣。這時,他的生活仍很艱苦,修業小學給他的工資每月只有幾元,吃飯以外就無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席和幾本兼作枕頭用的書。身上的灰長衫和白布褲。穿得很破舊。
毛澤東寫的一篇名為《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集中表達了他的觀點。這篇文章雄辯有力,通俗易懂,極富愛國熱情,盡管還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但與兩年前的《體育之研究》有明顯的不同。毛澤東開首便直刺中國社會現狀:“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他不再認為強健個人體魄是解救中國之關鍵。中國確需這樣一種修道士——毛澤東是他們中間的頭一個——來帶領中國走出黑暗。不過,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并沒有提出領導權。
他盡可能爭取廣泛的支持,號召各階層的民眾聯合起來,對壓迫他們的勢力“齊聲一呼”。這聯合將半靠自覺半靠組織,鞏固的團結是其關鍵。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發動民眾,下一次革命非喚起民眾不可。
文章提及了馬克思(“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以與毛澤東欣賞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生在俄國的, 叫做克魯泡特金” )相比較。毛澤東說,馬克思的觀點“很激烈”,克魯泡特金更溫和的觀點雖不能立見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優點是“先從平民的了解人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長沙,馬克思與其他一些革命理論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澤東期望一種更為公平的社會秩序。他有出色的組織才能,但是當時的毛澤東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理論形態。
毛澤東設想多種形式的聯合會匯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聯合的目的很簡明:“反對壓迫民眾的……強權者”,婦女、人力車夫、農民、學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這種聯合之內,沒有階級界限之分。
毛澤東以設身處地的口吻述說了各階層的苦難,而對學生之苦則最為激動:
我們的國文先生那么頑固。 滿嘴里“詩云”、“子曰”,究底卻是一字不通。他們不知道現今已到了二十世紀,還迫著我們行“古禮”,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著向我們腦子里灌。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談西方事務的文章筆力雄健,但有時也很怪異。他認為德國的“唯一出路”是與俄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聯合成一個“共產共和國”。巴黎和會后,他諷刺法國總理克里孟梭說:“無知的克里孟梭老頭子,還抱著那灰黃色的厚冊(暗指巴黎和約),以為簽了字在上面,就可當作阿爾卑斯山樣的穩固。”另外,黃雨川在《毛澤東生平資料簡編》中說,毛澤東當時并非像李銳所說。單獨負責《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
在學校時,毛澤東就造過現已與之不存在聯系的老師的反。現在,他要造社會的反。他信誓旦旦:
“我們倘能齊聲一呼, 必將這歷史的勢力沖破。”
毛澤東的文章受到李大釗舉辦的《每周評論》的贊揚(“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這激勵了長沙合作組織“湖南各界聯合會”在艱難中形成。
在開始公開自己的觀點中,毛澤東轉入一新的開端。讀書學習,在書頁上寫一萬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眾面前亮相則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行動,其言論將會造成后果。毛澤東不再只是探索周圍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這個世界。
軍閥張敬堯查封左派刊物的習性,就像看門人在能源危機時熄滅燈火一樣。一批全副武裝的士兵一夜之間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評論》扼殺了,它的主辦者湖南學生聯合會也在同一夜被取締。
當時各種小型雜志多如飛雀,過眼即逝。毛澤東很快又入主《新湖南》雜志,這家由湘雅醫學專科學校的學生主辦的雜志同樣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歡迎毛澤東去當編輯。該雜志創刊于6月,8月份由毛澤東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與《湘江評論》同樣的厄運。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國內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澤東的文章被長沙的主要報紙《大公報》采用,他作為政論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間,當地發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鮮事。
長沙有位趙女士準備出嫁,她不喜歡擇她為妻的那個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親是眼鏡制造商、男方的父親開古董商店——都極力促成這樁親事。娶親的那一天,趙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裝上了花轎。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從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嚨自殺了。
悲劇發生不到兩天,毛澤東寫的《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就見報了。在接下來的兩周時間內,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八篇論述婚姻、家庭的壓迫和舊社會的罪惡的文章。
如往常一樣,毛澤東從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會罪惡的根源。
他譴責社會:“趙女士的自殺,完全是環境所決定。”毛澤東言辭擲地有聲,“這種環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獨立,愛情的不能自由。 ”他把趙女士結婚的花轎稱作“囚籠檻車”。
從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的包辦的婚姻對他的影響,以及他母親的逆來順受。“大男子主義”已被列為中國革命的對象。
毛澤東以父親般的口吻寫下《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 他呼吁讀者 “振臂一呼”,砸碎迷信的枷鎖。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條信念。
“命定婚姻,大家都認作是一段美緣,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錯舉。 ”
自此時起,毛澤東終生都持反對在任何條件下自殺的思想。“截腸決戰,玉碎而亡,則真天下之至剛勇,而悲劇之最足以印人腦府的了。”像趙女士那樣自殺不是對腐朽的舊社會的反抗,它實際上迎合并維護了即將滅亡的舊道德秩序。毛澤東寫道:“與其自殺而死,毋寧奮斗被殺而死。”
毛澤東鞭撻了婦女貞節牌坊,這在當時給人印象極深:“你在哪里看見男子貞節牌坊嗎?”這個幾乎可以肯定還是童身的男子問道。接下來,他召集女學生走上街頭說服家庭主婦抵制日貨,爭取各方支持反對軍閥張敬堯的罷工。
毛澤東的思緒被新民學會的名稱牽回。婦女運動只是造就新民的開端。不過毛澤東正在逐漸接近這樣一個觀念,即建立幫蘋會應該是最終的目標。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與張敬堯的湖南政權處于沖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來了鎮壓。張敬堯的軍隊用刺刀和槍托驅趕在教育廣場焚燒日貨的人群。深夜召開的籌劃會議一個接著一個,毛澤東寫了一篇呼吁推翻親日派軍閥屠夫張敬堯的宣言。
13000名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宣言上簽了字,長沙大罷工開始了,勝負要見分曉了。張敬堯沒有被推翻——盡管他的統治動搖了——毛澤東和其他領頭的人大禍臨頭。
毛澤東決定離開湖南,以逃避張敬堯的追捕——張敬堯現在對他們懷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軍閥勢力那里去尋求對驅張運動的支持。毛澤東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個月是他收獲的季節,盡管并不盡如人意。
毛澤東是由新民學會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組成的驅張請愿團的團長。毛澤東還接受了《大公報》和其他報刊的任務,他這次不再是身無分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