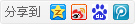京滬天地(四)
第一師范本身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校內學生中招募新的追隨者;靠學校的薪水維持少數學生領導人的生計;利用校友會寬敞的活動場所召集會議,并以文化書社的名義向每個與會者贈送10元錢作為禮物,還讓年輕人方便地出入圖書館,猶如出入公共汽車站一樣。第一師范對于毛澤東這個嶄露頭角的共產主義者來說像一個大家庭。
毛澤東的家人也被吸收進來。毛澤東的父親于1920年死于傷寒,終年52歲——此事毛澤東很少提起,除了說幾乎沒有人參加父親的葬禮外——毛澤東悄無聲息地接過了父親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澤民進入第一師范,讓三弟澤覃在一個很好的中學讀書,還把他繼妹澤建送到附近衡陽市一所師范學校。
這三人不久便參加了共產黨組織,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毛澤東像父親一樣時時把他們打發得團團轉。
毛澤東已不再是孤身奮斗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國的同志保持通信聯系。他在長沙這個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條大魚,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聯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澤東在1920年寫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贊成湖南自治問題的。這是毛澤東最終要支持地方主義嗎?是的。從其生氣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見毛澤東是怎樣一個人。
還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時候,他就與一位主辦《天問》周刊的湖南活動分子和湖南改造促進會取得了聯系。現在,譚延閩成了省長,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證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人室”。
毛澤東論述這個問題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還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文章《毛澤東選集》沒有收人)。
他也沒有為將來獨立的湖南確立社會目標,僅僅是讓湖南脫離壓在背上的重負。
毛澤東對湖南自治問題的議論是對自己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的運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稱為“外國”。他呼吁成立“二十七個小中國”,因為“大中國思想”是一種罪惡,阻礙了平民生活的“自然發展”。
誠然,毛澤東之所以贊成27個省都關起門來自治,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各省的小建設成功,一個更為強大和繁榮的中國才會存在,“這正像美、德兩國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對于一個已經是激進的信奉國家民族至上的人來說,轉而支持分省自治無疑是令人震驚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認為這是他的一個錯誤。他沉痛地寫道:“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北京,同其軟弱無能的“國民”政府(以及它嚴寒的冬天和對南方方言的歧視)一并受到毛澤東的抨擊。
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失去對湖南獨立自治的熱情。軍閥的更迭也動搖了這種激進的理想。譚延閩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統治者贊成自治,但反對通過自治解放民眾的任何意向。
數周后,毛澤東帶頭沖擊省議會,把掛在考究的墻壁上的條幅、旗子扯了下來。他認識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現存政治結構之外組織活動。
蕭瑜在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后見到了毛澤東。他們徹夜長談,淚眼相對,并發現彼此間存在鴻溝。毛澤東是親蘇俄派。蕭瑜則不是。毛澤東贊成強權,蕭瑜則擔心這會危及個人自由。
毛澤東決心組織民眾來奪取政權。蕭瑜則仍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學究。他對毛說:“像劉邦和項羽(漢朝的兩位敵) 那樣爭奪天下的爭斗,在耶穌基督和釋迦牟尼看來,就像街頭頑童為爭一個蘋果打架斗毆一般。”
毛澤東簡單地反駁道:“你不同意卡爾,馬克思的理論,多遺憾。”新民學會兄弟般的團結自此成為過去。
1921年初的一個大雪天,新民學會在文化書社開了三天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強調“變革”的目標,反對“改良”。他贊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對“通過幾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從法國歸來的大部分人反對他的觀點,一些繼續留法的人也寫信反對這一觀點。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會上宣布新民學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他贏得了自己斗爭的勝利。他轉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觀點類似的會員拉進了社會主義青年團,視新民學會如敝屣。
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已經分裂成兩派,這一結果使毛澤東與蕭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論戰已經為他們作了總結:“談論主義”還是“研究問題”?知識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體問題。還是在一種思想意識的指導下付諸一定的行動?
胡適教授為首的五四自由派堅持研究具體問題而遠離政治生活,李大釗教授為首的馬克思主義派則信守“主義” 。毛澤東無疑站在“主義”一邊,他希望發生分化。如果把五四傳統與某一具體思想形態聯系在一起就意味著會產生分裂的話,這種分裂是件大好事。
另一種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無政府主義乘時而“入”。一些敏感、篤信絕對自由的年輕人組成了自己的組織:湖南詩雨社、健學會、青年會和(最有影響的)勞工會。毛澤東對無政府主義的信條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時他曾為之傾倒,可現在他心中的馬克思已經驅逐了克魯泡特金,他狠命地與勞工會展開斗爭。
毛澤東以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類馬列主義的書籍為武器,抨擊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對方,嘲笑無政府主義者要“在24小時之內廢除國家”的蠢舉妄動。每當從無政府主義的陣營中爭取過來一人,毛澤東就把他引薦到組織嚴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來。
在北京時的孤獨和被人疏遠,使毛澤東傾向于接受無政府主義。現在,他正作為長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帶頭人大踏步地朝前邁進,并把無政府主義視為令人難容的東西。
1921年夏,毛澤東乘船北上。這次旅行是他在長沙10個月的組織活動的最高峰。作為準備階段,起先是成立馬克思主義與俄羅斯研究會以吸收有才干者,然后是新民學會的分化,接著是有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現在,重要的新步驟到來了。
在此前的幾個月中,毛澤東收到了數省共產主義小組織在聯絡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發來的很多指示。 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過上海這個港 15 城市參加計劃會議。
現在,毛澤東作為湖南兩位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湖南的兩位代表都是教師。另外還有來自其他五個省及(留學)日本的11名代表。
非常湊巧的是,在至漢口的船上毛澤東正好與蕭瑜同艙。作為朋友,他們爭議到深夜,此時的毛澤東正在研讀《資本主義制度概論》。堅固的友誼能戰勝判斷力嗎?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習慣仍保留在毛澤東的內心。
13位代表汗流浹背地來到上海的法租界,住進在博文女校已經訂好的房間(學校暑期放假)。他們大都是年輕人——平均年齡26 歲——他們中沒有一個是工人或農民。幾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澤東。
會議于7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棟裝有黑漆大門的灰紅色房子里舉行。這棟房子外表平平,底層沒有窗戶,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長兄的居所。全體代表——包括兩名來自共產國際的俄國特使——圍坐在起居室桌旁,桌上放著茶杯和文件。
毛澤東當時27歲。他頗為慎言,眼瞼下有一圈黑暈。作為代表,他穿著土布長衫像是一位來自湖南鄉下的道士。
有人記得毛澤東在發言時不停在聳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給人留下印象。
“他在講話時微笑著布下陷阱引誘對方上鉤,使與之辯論的一方無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發出一陣笑聲。”這會惹火那些認為有重要問題要談的人。
毛澤東常常不修邊幅。“你可以從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塵”,一位同僚回憶道。在飯店吃飯時,他用袖子擦去灑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襪子,或是讓襪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這種習慣保持了幾十年)。
對于毛澤東來說,這是令人十分激動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會的召開。他在著手湖南自治運動時曾寫道:“無論什么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現在他相信這種運動應該是布爾什維克式的,而他正與兩名布爾什維克同志,共產國際的馬林和遠東書記處書記尼科爾斯基同桌而坐。
參加會議的13位代表雖然各有不同的考慮,但終歸都受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的巨大激發。如果沒有俄國的影響和幫助,這種會議是不可能在1921年舉行的。
但是,長沙的情況不同于整個中國,更不用說莫斯科了。黨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與毛澤東這位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謀而合呢?
有跡象表明,湖南代表問題似乎成了會議的關注點。會議認定毛澤東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資格充當代表。毛澤東不愿傷害湖南老鄉的自尊心,于是找個借口讓何返回長沙,說長沙有緊急的事情需要何去親自處理。
會議的氣氛低沉,代表們并沒有感覺到自己是在親歷一重大歷史事件。炎熱的氣候使人疲憊不堪。一些代表感到頭昏腦漲,而更多的人則有意見沖突。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是這次散漫的會議上的活躍人物(在后來的歲月中,他對這次會議談得驚人的少)。
能否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虎頭蛇尾?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李大釗教授(當時仍在北京)和陳獨秀教授(當時在廣州)都沒有出席。
無論如何,這些代表不是經過考驗、有共同信念的團體。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華的東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時間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購物。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這13名代表也無法完全自主。會議的規模和時間基本上是由共產國際以及缺席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決定的。
在客廳桌子旁的代表們所發表的看法與毛澤東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這尤其使毛澤東不悅。
兩條路線正在形成。占統治地位的是共產國際的路線,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張國燾(他的故鄉就在韶山的另一邊)的支持:組織城市工人,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不與孫中山那遍布全國的國民黨發生聯系。
不贊成該路線的是漸進派。他們認為需要一個民眾教育時期,中國的城市工人數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資本主義,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事業,可以和孫中山合作。
毛澤東當時究竟是怎樣想的?誰充當組織領導者?采取溫和的方法還是激烈的方法?毛澤東對這兩派并非一無所知。那么,他為什么沒有堅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簡單,他當時心態復雜,漫元頭緒。俄國模式是他新的熱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這種熱情又很不穩固。在長沙反擊無政府主義的過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會主義,并滿腔熱情地加緊建立政黨。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條似乎有些動搖。

建黨初期的毛澤東
湖南的同志——全國 57 名共產主義者中長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嗎?這種新的觀點在韶山行得通嗎?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完全理解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一天,會場發現有可疑的來訪者。法租界偵探已在偵查這次會議。代表們決定轉移到上海南邊不遠的風景勝地去,于是會議在南湖的一只租來的游船上繼續舉行。
蕭瑜當時正取道上海回法國。奇怪的是他與毛澤東乘一列火車抵達南湖(蕭說這是毛的建議)。所有的會議代表同乘這列火車,但沒有坐在一起。毛和蕭閑聊,到南湖后同住一個房間。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勸蕭參加會議。
會議在游船上繼續進行,舒適華麗的16米長的游船飄蕩在水面。代表們品嘗著南湖的魚,決定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并且每個月向莫斯科的總部匯報。
那天晚上毛澤東很遲才回到旅店。他打開蚊帳,爬到雙人床上與蕭瑜睡在一起,他熱得滿身是汗但沒洗澡。
“代表們大多都不錯。”毛澤東用長沙老鄉之間談話的口吻對蕭說。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進入的更為廣闊的世界。“有些人還受過很好的教育,懂日語和英語。”毛澤東對蕭瑜預見道:“假如我們努力奮斗。再過三五十年,共產黨就有可能統治中國。”這種預言在當時簡直是空口說白話,蕭瑜當時也沒有多深印象,他擔心獨裁主義會步塵而來。
第二天早晨,毛澤東沒有去參加會議。他起得很遲,這是他的習慣。他起來后便與蕭瑜一起去杭州覽勝。他們在西湖附近的花園、小山和寺廟中度過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們爭了起來,蕭瑜羨慕山水的壯麗,毛澤東打斷他說:“這是罪惡產生之地,多少人用他們的金錢來干可恥勾當。”他們在杭州只住了一夜。毛澤東不久就回到長沙,擔任襁褓中的共產黨的湘區區委書記。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有見到過蕭瑜。
毛澤東從一個孤獨的山村走出來,現在竟能夠承擔以震撼世界的俄國革命命名的國際革命學說的責任。他以激奮心態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這種西方思想已部分構成他要求掌握社會變遷知識的初始階段。無政府主義思想在1919年強烈地影響著他。在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眾長對于他陶冶他那鋼鐵般意志的個性具有很高價值。確實,在1917年至1918年間,他似乎是個自由的個人主義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幾年中,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開始遠離自上而下的強烈的個人主義的鼓動做法,最終轉變到依賴下層革命。

浙江嘉興南湖游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