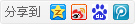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后來“三查三整”,也沒有采取這種形式。在革命戰爭時期,沒有人給我們發餉,沒有制造槍炮的工廠,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是依靠戰士,依靠當地人民,依靠群眾。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民主作風。但是,那個時候,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在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如果內部這么大鬧,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戰爭結束了,全國除臺灣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新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這種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現在容易說通了,在五月間那個時候,就很不容易說服人。北京三十四個大專院校,開了很多會才放開。為什么可以不怕?為什么放有利?大鳴大放有利,還是小鳴小放有利?或者不鳴不放有利?不鳴不放是不利的,小鳴小放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大鳴大放。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當然,個別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還有馮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燒共產黨,就下不得臺。那是少數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臺,可以下臺的。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民主黨派成員的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會主義革命對我們都是新的。我們過去只搞過民主革命,那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不破壞個體所有制,不破壞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只破壞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所以,有許多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可以過來。這里頭,有些人對徹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熱心,是勉強過來的;有些人對徹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這一關過來了。現在是過社會主義的關,有些人就難過。比如,湖北有那么一個雇農出身的黨員,他家是三代要飯,解放后翻身了,發家了,當了區一級干部。這回他非常不滿意社會主義,非常不贊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對統購統銷。現在開了他的展覽會,進行階級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錯誤。為什么社會主義這個關難過呢?因為這一關是要破資本主義所有制,使它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要破個體所有制,使它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當然,這個斗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長時間叫過渡時期,現在也還很難定。今年是斗爭的一個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來一個洪峰?象每年黃河的洪峰要來一樣,我看恐怕不是那樣。但是,這樣的洪峰,以后也還會有的。
現在,全國究竟有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和許多地方同志摸了這個底。在全國總人口中間,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這里包括地主階級,富農,一部分富裕中農,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甚至個別的工人、貧下中農。六億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萬人。這個數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們說要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有兩個出發點:第一,我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贊成社會主義。這里包括無產階級,農村里頭半無產階級的貧農,下中農,還有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多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以及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第二,在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里邊,最頑固的分子,包括極右派,反革命,搞破壞的,還有不搞破壞但很頑固的,可能要帶著頑固頭腦到棺材里面去的,這樣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萬。一千二百萬人,如果集合起來,手里拿了槍,那是個很大的軍隊。但是,為什么天下又不會大亂呢?因為他們是分散在這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這個農村,那個農村;這個工廠,那個工廠;這個學校,那個學校;這個共產黨支部,那個共產黨支部;這個青年團支部,那個青年團支部;這個民主黨派的支部,那個民主黨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處,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會大亂。
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什么范圍內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階級之間的斗爭呢?就是無產階級領導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我國無產階級數目比較小,但是它有廣大的同盟軍,最主要的就是農村里頭的貧農、下中農,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還要多一點。富裕中農大約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現在的富裕中農大體分三部分:贊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動搖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對的,占百分之二十。這幾年來,經過教育改造,地主、富農也有分化,現在也有不完全反對社會主義的。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為他們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事實不是那樣。在全國總人口中,贊成社會主義的,有百分之九十。我們要相信這個多數。經過工作,經過大辯論,還可能爭取百分之八,就變成百分之九十八。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當然,要注意,剛才鄧小平同志講了,它還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他們在農村說話沒有什么人聽。地主的名聲更臭。買辦資產階級早就臭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村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城市的上層小資產階級(一些比較富裕的小業主)和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就有些影響了。特別是這個知識分子吃得開,那一樣都缺不了他。辦學校要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辦報紙要有新聞記者,唱戲要有演員,搞建設要有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現在知識分子有五百萬人,資本家有七十萬人,加在一起,約計六百萬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萬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術的。右派翹尾巴也在這里。羅隆基不是講過嗎,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領導不了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他不說他是資產階級,一定要說他是小資產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我看,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是大字不認得幾個的工人、農民,也比他羅隆基高明得多。
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他們里頭的右派和中間派,對于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服氣的。講擁護共產黨,擁護憲法,那也是擁護的,手也是舉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氣的。這里頭就要分別了,右派是對抗的,中間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講共產黨這樣也不能領導,那樣也不能領導嗎?不僅右派有這個思想,中間派有些人也有。總而言之,照他們的說法,差不多就完了,共產黨非搬到外國不可,無產階級非上別的星球不可。因為你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嘛!無論講那一行,右派都說你不行。這一次辯論的主要目的,就是爭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間派,使他們懂得這個社會發展規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還是要聽文化不高的無產階級的話,在農村里頭要聽貧農、下中農的話。講文化,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不如他們,但是講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行。這可不可以說服多數人?可以說服多數人。資產階級的多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多數,是可以說服的。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工程師中的多數,是可以說服的。不大服氣的,過若干年,慢慢就會服氣了。
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上,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什么大鳴、大放、大字報,右派也可以搞。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 并沒有講什么大鳴, 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大”字。去年五月,我們在這里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后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問題都要鳴放,叫作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這個口號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間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究竟對那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百分之十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動搖的,至于堅決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亂得了呀?所以,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于社會主義。
我們不要怕亂,也不要怕下不得臺。右派是下不了臺的,但也還是可以下臺。按照辯證法,我看右派會一分為二。可能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大勢所趨,他們想通了,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了,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還要安排工作。少數極頑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著右派帽子進棺材,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這樣的人總是會有的。
右派這么鬧一下,使我們摸了一個底:一方面,贊成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爭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這樣的底,就心中有數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用我們這個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辦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現在波蘭發生的那樣的事件。我們不需要象波蘭那樣封一個刊物,我們只要黨報發一兩篇社論就行了。對文匯報,我們寫了兩篇社論批評它,頭一篇不徹底,沒有講透問題,再發第二篇社論,它就自己改。新民報也是它自己改。在波蘭就不行,他們那里反革命的問題沒有解決,右派的問題沒有解決,走那條道路的問題沒有解決,又不抓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所以封一個刊物就惹起事來了。我看中國的事情好辦,我是從來不悲觀的。我不是說過,亂不了,不怕亂嗎?亂子可以變成好事。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大亂一陣,事情就更好辦了。
我國解放以前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現在是一千二百萬工人。工人階級人數雖然少,但只有這個階級有前途,其他的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都要過渡到工人階級那方面去。農民頭一步過渡到集體化的農民,第二步要變為國營農場的工人。資產階級要滅掉。不是講把人滅掉,是把這個階級滅掉,人要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改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過來,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我講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如果不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險。現在許多人進了工會,有人說進了工會豈不就變成工人階級了嗎?不。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員反共嗎?進了工會不等于就是工人階級,還要有一個改造過程。現在民主黨派的成員、大學教授。文學家、作家,他們沒有工人朋友,沒有農民朋友,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比如費孝通,他找了二百多個高級知識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漢、無錫等地都有。他在那個圈子里頭出不來,還有意識地組織這些人,代表這些人大鳴大放。他吃虧就在這個地方。我說,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個,要到工人、農民里頭去另找二百個。我看知識分子都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農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農民中,不要輕易去找富裕中農做朋友,要找貧農、下中農做朋友。老工人辨別方向非常之清楚,貧農、下中農辨別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風有四個階段:放,反,改,學。就是一個大鳴大放,一個反擊右派,一個整改,最后還有一個,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風細雨,開點小組會,搞點批評和自我批評。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發表的整風文件中講和風細雨,當時許多人不贊成,主要是右派不贊成,他們要來一個急風暴雨,結果很有益處。這一點我們當時也估計到了。因為延安那一次整風就是那樣,你講和風細雨,結果來了個急風暴雨,但是,最后還是歸結到和風細雨。一個工廠,大字報一貼,幾千張,那個工廠領導人也是很難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時間,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辭職,說是受不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北京那些大學的黨委書記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那時候右派他們說,你們不能駁,只能他們鳴放。我們也講,要讓他們放,不要駁。所以,五月我們不駁,六月八日以前,我們一概不駁,這樣就充分鳴放出來了。鳴放出來的東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確的,有百分之幾是右派言論。在那個時候,就是要硬著頭皮聽,聽了再反擊。每個單位都要經過這么一個階段。這個整風,每個工廠,每個合作社都要搞。現在軍隊也是這樣搞。這樣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場”又要發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風,共產黨、青年團、民主黨派、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新聞記者、工程師、科學家里頭,又要出許多怪議論,資本主義思想又要抬頭。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掃,臉每天要洗一樣,整風我看以后大體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個把月就行了。也許那時候還要來一點洪峰。現在這個洪峰不是我們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們不是講過嗎?共產黨里頭出了高崗,你們民主黨派一個高崗都沒有呀?我就不信。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么一些人,你們民主黨派不是也出了嗎?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承認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認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響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說自己已經改造好了。章乃器說,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剝皮。我們說要脫胎換骨,他說脫胎換骨就會抽筋剝皮。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許多人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是干什么,為什么要這么搞,社會主義有什么好處。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為了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老知識分子會要逼得非變不可,因為新知識分子起來了。講學問,你說他現在不行,他將來是會行的。這批新的人出來了,就對老科學家、老工程師、老教授、老教員將了一軍,逼得他們非前進不可。我們估計,大多數人是能夠前進的,一部分是能夠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
無產階級必須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跟資產階級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一樣。一個階級的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國沒有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它資產階級專政怎么能行?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定要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包括從舊社會來的經過改造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右派中間那些不愿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有人說,要先專后紅。所謂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他在這個時候不紅,要到將來再紅,這個時候不紅,他是什么顏色呀?還不是白色的。知識分子要同時是紅的,又是專的。要紅,就要下一個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這并不是要讀很多書,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無產階級,什么叫無產階級專政,為什么只有無產階級有前途,其他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為什么我們這個國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為什么一定要共產黨領導等等問題。
我在四月三十日講的那些話,許多人就聽不進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說中國有五張皮。舊有的三張: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過去知識分子就靠這三張皮吃飯。此外,還靠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一個小生產者所有制即小資產階級所有制。我們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張皮的命,從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會主義革命是革后兩張皮: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小生產者所有制。這五張皮現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張久已不存,另外兩張也不存了。現在有什么皮呢?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張皮。當然,這又分兩部分,一個全民所有制,一個集體所有制。現在靠誰吃飯?民主黨派也好,大學教授也好,科學家也好,新聞記者也好,是吃工人階級的飯,吃集體農民的飯,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總起來說,是吃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飯。那五張舊皮沒有了,這個毛呢,現在就在天上飛,落下來也不扎實。知識分子還看不起這張新皮,什么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實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過去反對的人多,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天天反,說是“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害得大家生怕這個東西。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成無產階級世界觀,這要一個過程,而且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思想革命運動。今年這個運動,就是開辟這條道路。
現在有些機關、學校,反過右派之后,風平浪靜,他就舒舒服服,對提出來的許多正確意見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機關、學校就發生這個問題。我看,這個整改又要來一個鳴放高潮。把大字報一貼,你為什么不改?將一軍。這個將軍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個短時期,比如一兩個月。還要學,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風細雨,搞點批評和自我批評,那是在第四個階段。這個學,當然不是一兩個月了,只是講這個運動告一段落,引起學習的興趣。
反擊右派總要告一個段落嘛!這一點,有的右派估計到了。他說,這個風潮總要過去就是了。很正確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現在北京這個反右派的空氣,就比較不那么濃厚了,因為反得差不多了,不過還沒有完結,不要松勁。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們人數很少,擺到那里,擺他幾十年,聽他怎么辦。多數人總是要向前進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丟到海里頭去呢?我們一個也不丟。右派,因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所以是一種敵對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對待,其基本標志,就是不取消他們的選舉權。也許有個別的人,要取消他的選舉權,讓他勞動改造。我們采取不提人,又不剝奪選舉權的辦法,給他們一個轉彎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們。不是剛才講分兩種人嗎?一種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一種就是頑固到底,一直到見閻王。他說,我是不投降的,閻王老爺你看我多么有“骨氣”呀!他是資產階級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殘余、反革命是有聯系的,通氣的,彼此呼應的。那個文匯報,地主看了非常高興,他就買來對農民讀,嚇唬農民說,你看報紙上載了的呀!他想倒算。還有帝國主義、蔣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氣的。比如臺灣、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擁護的。美帝國主義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經跟各位講過,假如美國人打到北京,你們怎么樣?采取什么態度?準備怎么做?是跟美國一起組織維持會?還是跟我們上山?我說,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張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說這個話是極而言之,把問題講透,不怕亂。你美國占領半個中國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嗎?后來我們不是打出一個新中國來了嗎?我跟日本人談過,要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這個侵略對于我們很有好處,激發了我們全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提高了我國人民的覺悟。
右派不講老實話,他不老實,瞞著我們干壞事。誰曉得章伯鈞搞了那么多壞事?我看這種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羅同盟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最喜歡了。他們利用這兩個口號反對我們。我們說要長期共存,他們搞短期共存;我們說要互相監督,他們不接受監督。一個時期他們瘋狂得很,結果走到反面,長期共存變成短期共存。章伯鉤的部長怎么樣呀?部長恐怕當不成了。右派當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么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點職務不安排,一點工作不給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還可以當,副校長就當不成了。還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暫時也不能當,學生不聽。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學校里頭分配一點別的工作,讓他有所改造,過幾年再教書。這些問題都要考慮,是一個麻煩的問題。革命這個事情就是一個麻煩的事情。對右派如何處理,如何安排,這個問題請諸位去議一下。
各民主黨派什么情況,基層什么情況,恐怕你們這些負責人也不摸底。堅決的右派分子,在一個時候,在一些單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們看不見底。一查,其實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礬放下去,就看見了底。這次整風,就是放一把明礬。大鳴、大放、大辯論之后,就看得見底了。工廠、農村看得見底,學校看得見底,對共產黨、青年團、民主黨派,也都有底了。
現在,我講一講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經過兩年的實踐,基本要求還是那個四、五、八,就是糧食畝產黃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達到這個目標,這是基本之點。整個綱要基本上沒有改,只是少數條文改了。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如合作化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相應的條文就作了修改。有些過去沒有強調的,如農業機械、化學肥料,現在要大搞,條文上就加以強調了。還有條文的次序有些調動。這個修改過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經過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聯席會議討論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國農村中去討論。工廠也可以討論,各界、各民主黨派也可以討論。這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是中共中央這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不是章伯鈞那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
發動全體農民討論這個農業發展綱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勁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勁,加上城鄉右派一間,勁就更不大了,現在整風反右又把這個勁鼓起來了。范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后的說來,實現這個綱要是有希望的。我們中國可以改造,無知識可以改造得有知識,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綱要里頭有一個除四害,就是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不曉得諸位如何?恐怕你們也是有興趣的吧!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里頭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僅是農業計劃,還有工業計劃和文教計劃。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我們國家的面貌是會有個改變的。
我們預計,經過三個五年計劃,鋼的年產量可以搞到兩千萬噸。今年是五百二十萬噸,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鋼產量是一百六十萬噸,現在是一百七十幾萬噸,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幾萬噸。我們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萬噸,三年恢復時期搞到一百多萬噸,又搞了五年,達到五百二十萬噸,五年就增加三百多萬噸。再搞五年,就可以超過一千萬噸,或者稍微多一點,達到一千一百五十萬噸。然后,搞第三個五年計劃,是不是可以達到兩千萬噸呢?是可能的。
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那當然沒有信心。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釋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和農家。“三教九流”后來是泛指宗教和學術的各種流派,舊社會中也用來泛稱江湖上各種各樣的人。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0--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