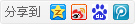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
第五章 戰略防御
這個題目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
(一)積極防御和消極防御;
(二)反“圍剿”的準備;
(三)戰略退卻;
(四)戰略反攻;
(五)反攻開始問題;
(六)集中兵力問題;
(七)運動戰;
(八)速決戰;
(九)殲滅戰。
第一節 積極防御和消極防御
為什么從防御說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失敗后,革命成了極深刻極殘酷的階級戰爭。敵人是全國的統治者,我們只有一點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斗。我們的進攻是密切地聯系于打破“圍剿”的,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御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復雜和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對于戰略防御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為敵人所嚇倒。
由于輕視敵人,許多游擊隊失敗了,紅軍對若干次敵人的“圍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擊隊初起,領導者對于敵我形勢往往看得不正確。他們看見自己在一個地方用突然的武裝起義勝利了,或從白軍中嘩變出來了,一時的環境很順利,或者雖有嚴重的環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輕視敵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敵強我弱,原是客觀地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講進攻,不講防御和退卻,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裝,因而把行動引到錯誤的方向。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為和這同樣的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廣東海陸豐區域的紅軍的失敗(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邊區的紅軍,在所謂國民黨偏師說的指導之下,使得反對第四次“圍剿”喪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實。
為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輕敵者相反,人們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卻方針,精神上同樣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裝。其結果或者是游擊隊失敗,或者是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者是根據地喪失。
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里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后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做了一萬二千多公里的長征。然而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正是后來在對付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采取消極防御路線的根源。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25),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
積極防御,又叫攻勢防御,又叫決戰防御。消極防御,又叫專守防御,又叫單純防御。消極防御實際上是假防御,只有積極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御。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御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中的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它。
后起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即德日兩國的軍事家中,積極地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御。這種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國革命戰爭的。德日帝國主義的軍事家們指出防御的一個重要的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而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于反動的統治階層乃至反動的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我們的情況不同。在保衛革命根據地和保衛中國的口號下,我們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地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者和被侵略者。蘇聯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的戰爭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就是在十月起義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正義戰爭的防御戰,不但有麻痹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動員落后的人民群眾加入到戰爭中來。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義之后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26),這是說乘敵不備而突然起義的群眾,應該不讓反動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反動的統治勢力打個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于已得的勝利,輕視敵人,放松對于敵人的進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滅敵人的時機,招致革命的失敗。這是正確的。然而不是說,敵我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當受敵人壓迫時,革命黨人也不應該采取防御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地說來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采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的戰爭是防御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對于我們,說進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說進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于打破“圍剿”。“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敵人的一次“圍剿”和它的又一次“圍剿”是銜接著的。這兩個階段中,防御的階段比進攻的階段更為復雜,更為重要。這個階段包含著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地就用不著戰略防御了。那時的方針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依靠于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到了那時,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東西了。
第二節 反“圍剿”的準備
對于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隊伍中曾經發生過的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里有一個困難問題,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當自己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御地位時,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我們難于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卻,和為著準備退卻的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準備過早,會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系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夸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對自己方面,不可夸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地估計到過去勝利的影響。
但是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后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卻,政治動員,征集新兵,財政和糧食的準備,政治異己分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的準備退卻,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著不利于退卻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于疲勞。這是在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紅軍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創造戰場,征集資材,擴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斗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據地的人民,關于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同時,關于敵人的弱點,紅軍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愿,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和人民全體為反對“圍剿”、保衛根據地而斗爭。除開軍事秘密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個可能擁護革命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說服干部。
征集新兵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和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和糧食問題,不待說對于反對“圍剿”是有重大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應當計算,主要的是紅軍,再則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斗爭中物資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分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于恐懼他們的叛變,而采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中立,并且組織民眾監視他們。只有對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于準備的放松,和由被敵人進攻所嚇倒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節 戰略退卻
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敵于國門之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27)。
春秋時候,魯與齊(28)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后來被曹劌阻止了,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請看歷史家左丘明(29)的敘述: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30)
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于民,敘述了利于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于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同時是說的戰略防御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31)、新漢昆陽之戰(32)、袁曹官渡之戰(33)、吳魏赤壁之戰(34)、吳蜀彝陵之戰(35)、秦晉淝水之戰(36)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37)、廣州起義(38)是失敗了,秋收起義(39)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后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地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后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著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發布之后,“左”傾機會主義者就向著正確的原則作斗爭,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確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后,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后,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啊!
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敵區或在我區敵區交界地方去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過去的東西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復,“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里產生的,而山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后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這里單說戰略退卻,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采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卻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過去卻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后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卻階段中取得下列諸種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有利作戰的陣地;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這個條件,對于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根據地的條件。并且由于這個條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區別;對于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所以“退卻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根據地這個特點,使紅軍的作戰比較一般的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也是使后來敵人不得不采取堡壘主義(40)的主要原因。
退卻的軍隊能夠選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進攻的軍隊不得不就我范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斗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卻,以就自己所欲的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的陣地,但無優良的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紅軍便不得不向根據地退卻。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和鉗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當著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就實行所謂“求心退卻”。退卻的終點,往往選在根據地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后部,依照情況來決定。這種求心退卻,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于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我們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卻的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于我軍,而我軍反優于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于根據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41),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
退卻的最后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于東而擊于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卻的終點,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卻所求的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以弱敵強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的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卻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于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時在全體形勢看來也對我有利時,則據此決定退卻終點,就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后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卻終點應該選在根據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陜甘第三次反“圍剿”時。有時須在根據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有時則在根據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系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于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干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于局部的和見于全體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開始反攻以為斷。
退卻終點,在根據地可以大體上分為前部、中部、后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強弱懸殊,我們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才主張向根據地退卻,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造成或發現利于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并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根據地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卻終點選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在理論上是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
白區退卻終點大體上也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在根據地前面,第二在根據地側面,第三在根據地后面。第一種終點,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和地方黨的分裂,即立三路線和AB團(42)兩個困難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集中兵力舉行反攻的。因為當時從贛撫兩河間(43)前進的敵人軍力,比起紅軍來優勢并不很大(十萬對四萬)。人民條件雖不如根據地,但陣地條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敵分路前進時各個把他擊破的。第二種終點,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閩贛交界的建寧、黎川、泰寧前進,這一路的力量又適合于我們的攻擊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第三種終點,同樣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敵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著退到會昌、尋烏、安遠地區(那里是白色區域),引敵更向南進,然后紅軍由南而北向根據地內部打去,這時北面根據地內部的敵軍當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為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對于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卻到根據地作戰,因為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進攻的辦法。
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的人們,反對戰略退卻,理由是退卻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壇壇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根據地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第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第五次“圍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擊的方法。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于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44)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45)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的政治影響,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響做代價。十月革命后,俄國布爾什維克如果依照“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意見拒絕對德和約時,新生的蘇維埃就有夭折的危險。
這種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于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對的,一切依照當時具體情況看來對于當時的全局和全時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局部和一時間,是應該捉住不放的,不然我們就變成自流主義,或放任主義。退卻要有終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絕不能依靠小生產者的近視。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布爾什維克的聰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當然,戰略退卻是有困難的。退卻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卻終點的選擇,政治上對干部和人民的說服,都是困難問題,都必須給予解決。
退卻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我們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的退卻,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那至少我們勝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響的。退卻過早和過遲,當然都有損失。但是一般地說來,過遲的損失較之過早為大。及時退卻,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動地位,這對于到達退卻終點以后,整頓隊勢,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有極大的影響。江西粉碎敵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戰役,都從容不迫地對付了敵人。惟獨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么慘敗之后,新的進攻來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如何選擇這個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敵我雙方大勢上去判斷,和前面說過的選擇準備階段的開始時機所用的方法一樣。
戰略退卻,在干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里而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干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由于干部沒有經驗,對于戰略退卻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圍剿”的整期,在這個問題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次反“圍剿”時,由于立三路線的影響,干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卻而是進攻。第四次反“圍剿”時,由于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干部的意見是反對準備。第五次反“圍剿”時,干部的意見開頭是繼續軍事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后來是變成了軍事保守主義。張國燾路線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區不能建立我們的根據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實例。經驗對于干部是必需的,失敗確是成功之母。但是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我們的戰爭吃這種虧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但是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后,在后來的幾次反對“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根據地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夠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地聯系于干部的信任與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說服干部。
戰略退卻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轉入反攻,戰略退卻僅是戰略防御的第一階段。全戰略的決定關鍵,在于隨之而來的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
第四節 戰略反攻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于在戰略退卻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比較敵人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各種條件造成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條件和形勢的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和形勢,具備著決定勝敗的可能性,但還不是勝敗的現實性,還沒有實現兩軍的勝負。實現這個勝負,依靠兩軍的決戰。只有決戰,才能解決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就是戰略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御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御戰的最后階段。所謂積極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
條件和形勢,不僅僅在戰略退卻階段中造成,在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著。這時的條件和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條件和形勢屬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時敵軍的更加疲勞和減員,不過是前一階段中疲勞和減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條件和形勢出現。例如,敵軍打了一個或幾個敗仗,這時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條件,就不僅敵軍疲勞等等,而是增加了敵軍打敗仗這個新的條件了。形勢也起了新的變化。敵軍調動忙亂,舉措失當,兩軍優劣之勢,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個到幾個敗仗不是屬于敵軍,而是屬于我軍,那末,條件和形勢的有利與否,也變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說,敵之不利減少,我之不利開始發生,以至擴大起來。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東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的一種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敵的條件和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條件和形勢去壓迫對方。
勝利者方面的努力和這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給敵人更大的損害,務求增加或發展有利于我的條件和形勢,而務求不讓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說來,決戰階段的斗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復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殲滅戰問題等。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于反攻說來,或對于進攻說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御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又都有若干的區別了。
因為這個理由,雖然這里把作戰的許多問題統統說在戰略防御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戰略進攻部門中只說些另外的問題,以避重復,但我們應用時,卻不可忽略其相同點,也不可忽略其差異點。
第五節 反攻開始問題
反攻開始問題,即所謂“初戰”或“序戰”問題。
許多資產階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略防御或戰略進攻皆然,而以防御為尤甚。我們過去,也曾經嚴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江西反對敵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圍剿”的作戰給了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研究一下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處的。
第一次“圍剿”時,敵人以約十萬人之眾,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之線,分八個縱隊向紅軍根據地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于江西省寧都縣的黃陂、小布地區。
當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不過十萬人,且均非蔣之嫡系,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二)敵軍羅霖師防衛吉安,隔在贛江之西。(三)敵軍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三師進占吉安東南、寧都西北的富田、東固、龍岡、源頭一帶。張師主力在龍岡,譚師主力在源頭。富田、東固兩地因人民受A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并和紅軍對立,不宜選作戰場。(四)敵軍劉和鼎師遠在福建白區的建寧,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敵軍毛炳文、許克祥兩師進至廣昌寧都之間的頭陂、洛口、東韶一帶。頭陂是白區,洛口是游擊區,東韶有AB團,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許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輝瓚、譚道源、公秉藩三師集中,不易決勝,不能最后解決問題。(六)張、譚兩師是“圍剿”主力軍,“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張又是前線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張師又分置兩處,我一次打一個師是絕對優勢。(七)張、譚兩師主力所在的龍岡、源頭一帶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條件好,能蔭蔽接近。(八)龍岡有優良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布就我,則陣地亦好。(九)我在龍岡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龍岡西南數十里之興國,尚有一個千余人的獨立師,亦可迂回于敵后。(一○)我軍實行中間突破,將敵人的陣線打開一缺口后,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為遠距之兩群。基于以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決定打而且打著了張輝瓚的主力兩個旅和一個師部,連師長在內九千人全部俘獲,不漏一人一馬。一戰勝利,嚇得譚師向東韶跑,許師向頭陂跑。我軍又追擊譚師消滅它一半。五天內打兩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畏打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二十萬人,何應欽為總司令,駐南昌。(二)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六路軍為最強或較強,其余均較弱。(三)AB團肅清,根據地人民全部擁護紅軍。(四)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從北方新到,表示恐懼,其左翼郭華宗、郝夢齡兩師,大體相同。(五)我軍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之建寧、黎川、泰寧地區擴大根據地,征集資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去,則限于贛江,戰局結束后無發展余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六)我軍人數較上次戰役時雖略減(三萬余),然有四個月的養精蓄銳。基于以上理由,乃決找富田地區的王金鈺、公秉藩(共十一個團)打第一仗。勝利后,接著打郭、打孫、打朱、打劉(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個仗,繳槍二萬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金鈺時,處于蔡廷鍇、郭華宗兩敵之間,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謂我們“鉆牛角”,但終究鉆通了。主要因為根據地條件,再加敵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師敗后,郝師星夜逃回永豐,得免于難。
第三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總司令。中路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路陳銘樞,駐吉安;左路朱紹良,駐南豐(48)。(二)“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每師九團,共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三師(49),四萬人。次是孫連仲軍,二萬人。余均非蔣嫡系,較弱。(三)“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于贛江而消滅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開始,為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后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贛南根據地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后由西而東,向敵之后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于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我軍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發覺,陳誠、羅卓英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里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后,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一個師及郝夢齡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后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50)。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線于黃陂,猛力并進,找我作戰,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軍乃于蔣、蔡、韓軍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由東面回到西面之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饑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卻了。我又乘其退卻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第四次“圍剿”時的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黃南部地區,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于宜黃南部地區。兩役繳槍萬余,這個“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占領了黎川。我卻企圖恢復黎川,御敵于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后輾轉尋戰于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我軍作戰的經驗,證明處在防御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斗,關系非常之大。第一個戰斗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于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后的一個戰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敵,確有把握而后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一次反“圍剿”時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反“圍剿”時,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于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圍剿”雖是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回其側后的計劃,但我們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于在蓮塘打著第一個好仗。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卻步驟,終于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只有第五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消滅敵一個師)之后,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于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只算敗了(例如第五次“圍剿”時的洵口戰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將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后,或萬一反攻失敗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于政治是不利的,對于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沖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張國燾路線的戰略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地就在于沒有作到這一點。總之,退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卻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