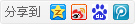李敏(1936年─)原名毛嬌嬌,生于陜西省志丹縣,籍貫湖南省湘潭縣,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與第二任妻子賀子珍所生的女兒,毛岸英與毛岸青的同父異母妹妹,李訥的同父異母姐姐;國民黨軍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化名“李得勝”,轉戰陜北,繼續與國軍對抗,于是毛嬌嬌便跟隨父親改姓李,全名為“李敏”,“敏”字取自《論語》中的「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
李敏(1936年─)原名毛嬌嬌,生于陜西省志丹縣,籍貫湖南省湘潭縣,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與第二任妻子賀子珍所生的女兒,毛岸英與毛岸青的同父異母妹妹,李訥的同父異母姐姐;國民黨軍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化名“李得勝”,轉戰陜北,繼續與國軍對抗,于是毛嬌嬌便跟隨父親改姓李,全名為“李敏”,“敏”字取自《論語》中的「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李敏在1959年與孔令華結婚,在1962年誕下長子孔繼寧及在1972年誕下次女孔東梅。孔繼寧和孔東梅現在商界發展。2006年,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周年前夕,李敏與其他毛澤東遺屬一同赴朝鮮拜祭在朝鮮戰爭陣亡的哥哥毛岸英。
1936年冬,李敏出生在陜北的保安縣。趕來賀喜的鄧穎超看她長得又瘦又小,憐愛地說:“真是個小嬌嬌呀!”于是,在一旁的毛澤東當時就給孩子起了個小名“嬌嬌”。但幾個月之后,賀子珍遠赴蘇聯,把嬌嬌留在了延安。4歲時,嬌嬌被送到蘇聯,和賀子珍一起生活。1947年,賀子珍終于帶著嬌嬌回到中國,住在哈爾濱。那時候,嬌嬌對中文半懂不懂,是個十足的“洋娃娃”。后來,毛澤東派人接嬌嬌回北京,她還半信半疑。1949年初夏,嬌嬌回到了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十分高興,逢人就說,“我家有個會說外國話的洋寶貝”。送嬌嬌上學時,毛澤東給她取了一個正式的名字李敏。嬌嬌在陜北時,毛澤東曾化名為“李得勝”。
1959年,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期間,李敏和北京航空學院的高材生孔令華結了婚。孔令華是炮兵副司令孔從洲的兒子,也是李敏在中學時的同學,兩人彼此了解,情投意合。這樁婚事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 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一年后,李敏生了個男孩,也就是孔東梅的哥哥孔繼寧。毛澤東經常抱抱小外孫。自從搬出中南海,李敏夫婦出入中南海的證件就被收回了。要進中南海得在門口先聯系,通報后才能進入,有時候等了半天還進不去。1964年,李敏夫婦搬進了兵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平民生活。毛澤東從患病到逝世,李敏總共見過他三次。李敏第三次見到父親,是在父親逝世前幾天。他拉著李敏的手說:“嬌嬌你來看我了?你為什么不常來看我呢?”李敏無言以對,只能默默流淚。
離開毛澤東后,李敏的日子一直過得很簡樸,有時甚至很清苦。李敏夫婦一直都是靠工資吃飯,他們自從搬離毛澤東的住處就自己做飯,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樣。而當時,李敏和丈夫都在國防科委上班,工資不高,不僅要撫養兩個孩子,每個月還要另外寄些零用錢給母親賀子珍。
文革經歷
摘自:《生活時報》2001年4月6日版《我的父親毛澤東》(作者李敏)。
李敏自述: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因為我也生活在那個年代,當然也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了。在人們的心目中,好像我是個最走運的人,認為我是毛澤東的女兒,就不會挨批挨斗。其實錯了。我也同樣離不開那個時代,離不開當時的政治形勢,我也同樣受到批判,被勒令交待問題,被列入“五一六”分子的名單中。孔令華也被說成是埋在我爸爸身邊的定時炸彈,沒完沒了地挖了起來,不也同樣挨批挨斗嗎!后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我倆同時受到批判。不過我倆也有不一樣的時候,就是他戴過高帽子,我沒有戴過。但這比起一些挨批挨斗的老干部來,我個人受點沖擊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在我處境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拋開個人的得失,為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為保護一些老同志盡了我一個公民、一個黨員、一個軍人的職責和義務。
我三步并作兩步地走到爸爸的住處。誰知剛剛進門,就碰上了江青。真是冤家路窄。尖酸刻薄的江青看見了我,就陰陽怪氣地挖苦我說:“小保皇回來了呀!怎么偏偏在這時候回來呀!是不是想摸底?”一進家門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江青的話,讓我爸爸聽到了。爸爸生氣地說:“你去告訴她,就說你是回來摸底的,看她怎么辦。”
“文革”進入高潮,批判會在步步升級。那些殘酷批斗老干部的會議及方式,對我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我非常反感也感到了極大的苦惱。當看到斗蕭華同志并讓他坐“噴氣式”時,我無可奈何,就和坐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志寫了一張條子,“要文斗,不要武斗”傳給主持人。但這卻無濟于事,他們仍然我行我素,繼續采用這種殘酷的批判方式。當我看到羅瑞卿同志被用筐子抬到臺上批斗時,我實實在在不忍再看下去,就站起來,當即退出了會場,以此表示我的不滿與抗議。我想,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不一會兒,周圍許多同志也相繼退出了會場。我想,他們的心情肯定和我是一樣的。作為一般工作人員,我們也只能以此表示反對了。又如,原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同志,是因心臟病去世的。當時,有些人說他是自殺,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機會跟爸爸講了這件事。爸爸說:“趙爾陸是個好同志,是井岡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護他。我問爸爸:“能不能轉達?”爸爸說:“能。”我回到機關后,向有關領導轉達了爸爸的指示。這也算是我為保護老干部做了一點工作吧。
1968年初,因為北航老找國防科委領導提出要“勒令”我交待問題。沒辦法,領導就讓我跟機關的同志到北京郊區王四營公社參加農業勞動去了。直到麥收之后,我才又回到國防科委機關。1969年10月25日晚,我又隨國防科委機關干部被“一鍋端”到河南省遂平縣蓮花湖的“五七”勞動農場。1971年初,爸爸對我說過:“你和李訥到中央辦公廳江西省‘五七’干校勞動去吧。”我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同志說:“我是國防科委的干部,還是到科委干校去吧。”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和同志們由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團罪行的過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們所謂的“國際口‘五一六’”的黑名單中。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們意料之外的。1973年12月,國防科委黨委為我們這些黑名單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決定。 原以為從此以后我的日子會好過些,就會平安無事了。誰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告訴我說:“江青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看看,我又要倒霉了。現在看來,江青借這個機會報復我、整我那真是輕而易舉的事了。對她來講,這只是舉手之勞。但既然爸爸告訴了我,我還是防著點好。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見到了爸爸。談到當時的形勢時,我說:“令華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隨叫隨到’,他還要戴高帽。”我想,爸爸聽了這話,可能會安慰令華幾句,給他寬寬心。誰知,爸爸聽了后,沒有說話,只是沖著我倆笑,而且笑得很開心。就像那年我們為他祝賀生日一樣,樂呵呵地笑出聲來,而且聲音還挺大。“經風雨見世面嘛!”笑過之后,爸爸只說了這樣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