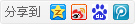1920(3)
4月1日、4日 兩次致信留法的蕭子升,并寄送平民通信社稿件和《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信中說,“人才要講經濟,學問、游歷要講究多方面”,新民學會會務的“進行注意潛在,不出風頭,不浮游大碼頭”。
4月上旬 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東街中老胡同商討結束在京驅張活動問題。這時,直皖兩系軍閥利害沖突日趨劇烈,吳佩孚通電全國控告張敬堯搜刮政策。張敬堯處在四面楚歌之中,湘軍湘人有聯合驅張之勢。會議決定,在北京的驅張代表,除留羅宗翰等少數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別到武漢、上海、廣東及回湘繼續進行驅張活動。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有密切聯系,用心閱讀他們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熱心地搜尋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這時,毛澤東較多地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有比較正確的理解。〔1〕
〔1〕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羅章龍在一九九○年三月曾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產黨宣言》不長,全文翻譯了,按照德文版翻譯的,我們還自己謄寫,油印,沒有鉛印稿,只是油印稿。我們醞釀翻譯時間很長,毛主席第二次來北京后看到了。”
4月11日 離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處參觀游覽,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還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達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號。
5月8日 同新民學會會員蕭三、彭璜、李思安等,為歡送即將赴法的陳贊周等六位會員,在上海半淞園開送別會。送別會討論了新民學會會務問題,確定“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為學會態度。“介紹新會員入會,此后務宜謹慎”,議決吸收新會員的條件為:一純潔,二誠懇,三奮斗,四服從真理。送別討論會延至天晚,繼之以燈。中間“在雨中拍照,近覽淞江半水,綠草碧波,望之不盡”。
5月11日 與在滬會友送陳贊周等六人赴法,同他們握手揮巾,道別于黃浦江岸。
5月 應彭璜之邀,與一師同學張文亮等一起試驗工讀生活,在上海民厚南里租幾間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過著一種簡樸的生活。一個月后,彭璜寫信給湖南的岳僧說,經過“考查北京已成各團的現狀,調查社會生活的現實,才覺得這種工讀的生活,卻也不容易辦到”,上海工讀互助團“現在竟不能說不失敗”!
6月7日 致信黎錦熙,說“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信中強調自學和博學,寫道:“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規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國語真是一張門戶,不可不將它打通,現在每天讀一點英語,要是能夠有恒,總可稍有所得。我對于學問,尚無專究某一種的意思,想用輻射線的辦法,門門涉獵一下。頗覺常識不具,難語專攻,集攏常識,加以條貫,便容易達到深湛。斯賓塞爾最恨國拘,我覺學拘也是大弊。”對于“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只這三科。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起,漸次進于各家;英文最淺近讀本每天念一短課;報則逐日細看,剪下好的材料。”信中還說,旅京湖南學會,是一種混合的團體,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體的鮮明的熱烈的東西,易于見效,興味較大。我覺得具體、鮮明、熱烈,在人類社會中無論是一種運動,或是一宗學說,都要有這三個條件,無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國,便是因襲,不是創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在談到自己的性格時,信中說:“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
6月9日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說張敬堯禍湘,“欺人太甚,有些難忍”。“湘人驅張,完全因為在人格上湘人與他不能兩立”。
6月11日 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十二日,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十四日,湘軍總指揮趙恒惕到長沙。十七日,湘軍總司令、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闿到長沙。
同日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文章指出,湖南驅張運動將要完結,“湖南人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怎樣廢去督軍,建設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應該積極注意的大問題”。“湖南人有驅湯薌銘、驅傅良佐、驅張敬堯的勇氣,何不拿點勇氣把督軍廢去”。文章提出中國民治的總建設,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決,合起來便可得到全國的總解決。“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勢,兼想一想八九年來自己經過的痛苦,發狠地去干這一著。”
6月18日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指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
6月23日 以湖南改造促成會的名義復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張。闡明湖南改造的要義在于“廢督裁兵”、“建設民治”。說中國二十年內沒有實現“民治之總建設”的希望,在此期間,湖南應實行“自決自治”,“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筑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于湖南領域以內”。信中向打著“湘事湘人自治”旗號的譚延闿、趙恒惕政府,提出兩點要求:“第一,能遵守自決主義,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將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義,自認為平民之一,干凈洗脫其丘八氣、官僚氣、紳士氣,往后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最重要者,廢督裁兵,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此信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申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為題全文發表。
6月30日 致信羅章龍,告以在上海的見聞。信中談到要將湖南的事情辦好,搞自決自治。羅章龍贊成毛澤東的主張,并復信說:“你們這一年的勞苦,代價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
6月 在上海期間,同陳獨秀討論過組織湖南改造促成會的計劃和自己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1〕。這時,陳獨秀正在上海籌備組建共產黨。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2〕
〔1〕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中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1〕關于此事,章含之在《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曾有一段回憶,她說:一九六三年毛主席突然提出“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從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春節初二這天,主席用自己的稿費必定派秘書送兩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滿累計兩萬元。主席還說:這個錢是給你們那位老人家的補助,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還“利息”,這個錢一直送到行老不在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