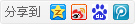媒體報道
毛泽东文革过错或因脑血栓

1976年6月,中共中央公告,毛澤東因“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不再會見外國來訪人士。這條簡短的消息引發了國人普遍的猜測與巨大的擔憂:再偉大的領袖也有老病這道坎。五年以後,國門打開之初,有一本《病夫治國》暢銷讀書界。剛從“文革”噩夢走出的國人,最感興趣的是其末章《周恩來-毛澤東》。據該書說,1965年,正當“文革”山雨欲來之時,毛澤東診斷出大腦血栓堵塞;其後,年復一年,“便被這種疾病所控制”。該書暗示,這種疾病容易導致患者“脾氣變壞”,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過錯似與此不無關係。毛澤東與“文革”的內在宿命,原因未必那麼簡單,但該書考察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二十六位現代領袖如何在疾病狀態下治理國家的,無非試圖證明:“如果這些政治家身體健康的話,某些決定將是不同的。”(324頁)
《病夫治國》說得不錯,“任何一位醫生都可以和醫學專欄作家或歷史學家一樣,對更好地認識歷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貢獻。”(324頁)但倘若落實到中國古代史領域,問題卻不樂觀:“史學家大都不懂中醫醫理,而中醫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醫學史料。”(王曾瑜《絲毫編》623頁)然而,《病夫治國》大陸初版三十年後,一位有醫學背景的史學博士,在導師啟發她閱讀該書之後,豁然憬悟:“病夫治國現象,在醫療條件相當發達的現代尚且如此,更何況醫療水準相對不高的宋代。”(第1頁)於是,發願在宋史領域完成對疾病史與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便有了這部《宋代皇帝的疾病、醫療與政治》(下稱《皇帝病》)。作者發揮了自身橫跨醫學、歷史兩大學科的專業優勢,“除了利用中醫學理論對宋代皇帝病症進行排比分析,還特別重視利用現代西醫學的成就,如內科學、外科學、心理學、精神病學、醫學免疫學、醫學統計學等理論進行論析”(10頁),從皇帝的疾病聯繫到對政治的影響,為歷史研究添加了一個解釋層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儘管有了合適的研究者,史料仍是最大的考驗。歷代皇帝的疾病與醫案,從來是宮禁頂級機密。宋高宗就曾下詔,凡是御用的湯藥醫方,“不許傳錄出外”。清代雖也如此,但宮廷醫案基本存檔,民國以後便漸為史家所用。反觀宋代,不僅未見有皇家醫案傳世,甚至缺乏精准的記載,現有的片段也都附著於政治史料,而且往往諱飾失實。有鑒於此,著者通過對全部文獻的搜羅考證,一網打盡了宋代君主的疾病史料,採取“倒過來做”的思路,即憑藉政治史料的片言隻語,再借助現代醫理來反推或判斷其病症真相。為了讓研究擁有更堅實的基礎與更廣闊的視野,著者還統計了中國史上皇帝的壽命、疾病與死因,並據《宋史》立傳人物統計出宋代上層男性的平均壽命。
二
《皇帝病》統計了有生卒可考的三百一十位中國皇帝,主要結論如下:其一,自殺與他殺等非疾病死亡的一百人,因病死亡的二百一十人,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其二,在皇帝常見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藥中毒、酒精中毒、春藥中毒等),腦血管疾病與精神疾病分列二三位。其三,不計自殺或他殺的一百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壽命接近四十八歲。其四,從平均壽命的朝代曲線來看,秦漢皇帝最低,僅三十四歲;隋唐逐步上升到四十四歲;宋遼金君主四十八歲,與歷代皇帝壽命均值相當,達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於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五十三歲。
總體而論,宋帝群體的個體素質與文化修養,在歷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從疾病遺傳學來說,上天對天水趙氏卻並不眷寵。宋代皇帝的平均壽命為四十九點七六歲,明顯低於當時上層男性的壽命均值六十四點四七歲。難怪有論者撰文時,取了個抓人眼球的標題——《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2010年第三輯,李尋、李海洋)。
現代醫學界定的疾病,不僅指有病理變化的器質性疾病,還包括與精神因素相關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趙宋皇族的遺傳基因中,腦血管疾病與精神性疾病是揮之不去的二豎。北宋真宗、仁宗、英宗與神宗,連續四代都有腦血管疾病的嚴重症狀:中風引起言語蹇澀,失語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腦血管疾病,雖然那在他當太上皇以後。宋光宗似乎也有類似症狀。《皇帝病》認為,宋代皇族多屬A型性格,其自責嚴苛、脾氣急躁的個性最易導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誘發血壓升高,大大增加心腦血管病的發病幾率(90、93頁)。
在論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時,《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敗,兩宋諸帝先後恐遼、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謂一脈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勢,也影響到性格遺傳,這與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懼症是互為因果的。但也有學者認為,狂躁症與憂鬱症(即恐懼症)實為趙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現。狂躁症主要症狀是“小不如意就狂怒異常,以致殺人放火。而且是間斷發作,不發作時頭腦清醒”(劉洪濤《從趙宋宗室的家族病釋“燭影斧聲”之謎》,《南開學報》1989年六期)。有一則史料也曾引發過筆者的聯想。史載,宋太祖“惑一宮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這種暴戾之舉,與趙匡胤一貫為人大相悖逆,洩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殺人的隱性病灶。
作為印證,還有宋太宗長子趙元佐的“狂疾”。他突然聽聞叔父趙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後一度好轉,但有一次其父沒讓他出席重陽諸王宴,便“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宮”。他在真宗朝病情穩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與太宗後裔,這種“狂疾”一再呈現顯性狀態:太祖之孫趙從讜“射殺親事官”,禁閉別宅竟自剄而亡;太宗曾孫趙宗說也酷虐地“坑殺女僕”,閉鎖幽死。
當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會出現狂躁與抑鬱交替發作的“雙相障礙”。最明顯的就是宋光宗,先是憂懼成疾,禪位後或嗔罵,或慟哭,竟至掄臂怒毆自己的皇后,顯然屬於狂躁症,最後成為“瘋皇”。
除了困擾趙氏宗室的兩大遺傳病,寧宗與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宮廷秘密。宋寧宗有消化功能紊亂症,關注飲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誕之舉卻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紙為底、青紙為邊,讓人糊了兩扇屏風,其上分書“少飲酒,怕吐”與“少食生冷,怕痛”。每次巡行後宮,就命兩個小宦官各扛屏風前導開路,到達後正面豎好,有勸酒食者,就手指屏風示意。作為堂堂大國之君,竟不能應對金朝使者的入見禮儀,“陰使宦者代答”,其治國能力不言而喻。晚宋周密毫不客氣認定,“寧宗不慧而訥於言”。《皇帝病》判斷,“宋寧宗為魯鈍型精神發育遲滯,相當於輕度的精神發育不全”(53頁)。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親侄,《宋史》說他“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虛飾之言。據《癸辛雜識》,度宗出生後“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分明是發育不良,智力呆滯,長到七歲還不會說話,恰恰證明他的語言發育能力遠比正常兒遲緩。但宋理宗絕後,為不讓皇位轉入遠支宗室,竟偽稱神人托夢:“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宋度宗二十一歲立為皇太子,理宗為其創造了最好的教育條件,他也“終日手不釋卷”,不可謂不用功。但每次請安時,理宗總問他日課,“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之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玩味這段為尊者諱的記錄,不難讀出背後的事實:度宗的智商實在不敢恭維,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繼之以怒”。《皇帝病》據“以其母賤,遂服墜胎之藥”的史料,認為在圍生期內,“許多藥物都可導致胎兒精神發育遲滯”,度宗較之寧宗,“精神發育遲滯更為嚴重”(53頁)。
在兩宋諸帝中,宋高宗活到八十一歲,最稱高壽。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揚州行宮白晝行床笫之歡,突接金軍奔襲的戰報,驚嚇之下,立馬陽痿,時年二十三歲。其後,他為恢復性功能而“垂意藥石事”,服用御醫王繼先開出的仙靈脾(即淫羊藿)。研究者認為,該藥方雖有補腎壯陽的“偉哥”性能,但“應有互不協調的成分,使高宗無藥則不能行房,服藥卻不能生育”(王曾瑜《絲毫編》288頁)。他碰上了迴圈性悖論:不重振雄風便不能生仔,要重振雄風則必須服藥,但服藥行房就無法生仔。性功能障礙與不育症伴困擾其終生,他終於絕了後。
《皇帝病》探討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歸結為遺傳因素、環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國禎說,“疾病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為尤甚。”在酒色誘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說嗜酒。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與斧聲燭影前夕的兄弟酣飲,都與嗜酒有關。宋真宗“飲量無敵”,愛以巨觥召綽號“李萬回”的侍讀拼酒。宋光宗為太子時,嗜酒癖好就名聲在外,即位後更是“宮中宴飲,稍失節度”,李皇后也好這一口,宋寧宗的魯鈍或是受胎時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飲宴過度”,以致時人以“天地醉經綸”譏之。宋度宗“既立,耽於酒色”。
再說縱欲。宋仁宗親政之初,尚、楊二美人有寵,每夜侍寢,“體為之弊”,“臨朝則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風,也與隆冬臘月寵倖宮婢時中了風寒有關,終至一病不起。宋哲宗二十五歲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醫診斷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認為,這種滑精症狀“與其年少時過多親近女色密切相關”(58頁)。宋徽宗後宮妃嬪數以萬計,還別有“性趣”,“五七日必禦一處女”,他禪位後放出的宮女竟多達六千餘人。宋高宗“好色如父”,還道貌岸然聲稱“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揚州之變後,他倚賴壯陽藥繼續縱情聲色。直到做了太上皇,還召入孫女級的美女供其泄欲。他死後,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宋理宗沉迷女色,對宮嬪“泛賜無節”,晚年為滿足色欲,還把官妓召入宮中。在東宮時,宋度宗便“以好內聞”,凡“禦幸”的宮嬪,按宋制次日就應登錄謝恩,他即位後,居然“謝恩者一日三十餘人”,縱欲之甚,怕也破了紀錄。
縱觀宋帝的症狀與病因,凸顯出君主專制的非人性,也即黃宗羲所激烈抨擊的:“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
三
除了禪讓、政變或易代,君主專制具有終身制與世襲制兩大特點,而君權的獨一無二規定了皇帝實行一人的獨裁,即所謂“乾綱獨斷”、“在予一人”。君主政體的命運必然是一人決定天下治亂,也就難怪其治下臣民總期盼能遇上聖君明主。然而,在世襲制下,聖君明主首先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有幸遇上,也難保終其一生的任何決策都是偉大、英明與正確的。倘若結合疾病的論題,不僅君主個人的思想、氣質、才略與能力,他本身的心理、性格、健康與智力,也都關係其帝國的安危興衰,決定其子民的休戚禍福。終身制與世襲制命定了君權的不可分割與不可轉讓,但由於君主的健康原因,君權異化的歷史困局卻一再重現。皇帝疾病時的君權異化,主要表現為病夫治國、後妃幹政、近幸得勢、權臣擅朝、傳承危機等亂象,而且往往諸症併發。最著名的就是白癡晉惠帝與悍後賈南風胡作非為,新老外戚爭權,激成“八王之亂”,西晉短命而終,天下生靈塗炭。宋帝疾病的負面影響雖未如此之甚,但仍具有君主專政的共性,各種症狀如出一轍。
其一,病夫治國。
自天禧三年(1019)起,宋真宗數度中風,幾至“不豫”(皇帝病危專用詞)。臨死那年,再次中風,宰相無奈朝見於寢殿,他已失語,對上奏只能“頷首數四”,表示贊同。仁宗、英宗與神宗的晚年,這種因嚴重中風而不能理政的局面一再重演。而宋神宗對西夏倉促用兵終致慘敗,與其“切於求治”而“速致太平”的急躁性格也是息息相關的。哲宗晚年,“疾勢未退”,“脈氣微弱”,竟至不能正常會見宰執與接待遼使。
南宋中期後,迂劣之君接二連三,因病誤國幾成常態。宋光宗以精神病者而君臨天下達兩年半之久,昏政不斷,亂局頻現。他召回了初政時親自放逐的“大惡近習”陳源,發還抄沒的家產,讓其重當宦官班頭。自發病後,他懷疑宗戚大臣的訃報都在誆騙自己,四川統帥死了半年,他認定還活著而拒絕派新帥。宋光宗疑懼與妄想太上皇宋孝宗要廢黜或加害於他,拒絕前往朝見,一再釀成過宮風波。太上皇去世,他作為兒子竟拒絕出主大喪,釀成人倫鬧劇。
作為唯一的皇二代,宋寧宗理所當然地承繼皇統,史官說他“臨朝淵默寡言,於事少所可否”,行事堪稱癡騃。他明知東宮老師陳傅良是好人,問今何在,權臣韓侂胄唯恐其起用,托言“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他便不復召用。殿前司屬官華嶽反對史彌遠專政,逮捕入獄,擬定斬首。複奏時,寧宗久聞其直名,想貸他一命,史彌遠奏稱“那就與減一等”,寧宗不知斬首減一等是杖斃,竟表示同意。史彌遠上下其手,將華嶽活活杖死。
其二,後妃幹政。
祖宗家法對宋代後妃亂政有防範作用,但君主身染頑疾,卻為其開啟方便之門。宋真宗後期深為腦血管病所苦,劉皇后警悟幹練,趁機“預政於內”。他讓皇太子協理朝政,卻依舊“事皆決於後,中外以為憂”。宋真宗死後,劉皇后乾脆走向前臺,以皇太后臨朝達十二年之久。
宋光宗患上精神病,也給李皇后亂政開了綠燈。她不僅讓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還大肆推恩,連娘家門客都補了官。李皇后還挑唆光宗與太上皇的關係,為過宮事件推波助瀾。如果說劉皇后預政,後人還不乏好評,悍後李鳳娘幹政則讓紹熙稗政雪上加霜。
宋寧宗先天顢頇,楊皇后與史彌遠遂得以內外呼應,策劃政變。她代擬御筆,拘押了大臣韓侂胄。宋寧宗得知消息,打算追回侂胄,她以死威脅,迫令就範。楊皇后在誅韓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也導致了史彌遠的長期專政。
宋度宗沉溺酒色而不問朝政,與宋寧宗相比一蟹不如一蟹。他寵倖一大批嬪妃,昭儀王秋兒最受親近,“批答畫聞”,“皆出其手”,連批答文書的大權也拱手交出。
其三,近幸得勢。
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與理宗,都有近幸弄臣恃恩獲寵,而高宗朝的城狐社鼠尤其猖獗,與其寡人之疾大有干係。他自揚州驚變,性病便成心病。約此前後,世代為醫的王繼先成為御用醫官,他“喜諂佞,善褻狎”,不久就以“用藥有功”、“實有奇效”而讓龍心大悅,其拿手戲無非為這位好色之君配製壯陽藥。服藥以後,宮闈勾當自然少不得貼身內侍,宦官張去為也因緣際會,大獲高宗的青睞。秦檜欲擅權而未固寵時,還要巴結王繼先在高宗左右打點。史稱:
繼先遭遇紹興中,富與貴冠絕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侔。其權勢之盛與秦檜相埒,張去為以下尤不足道。而通關節,肆誅求,強奪婦女,侵漁財利,則檜所未嘗為也。
當時人說,宋高宗把國事託付秦檜,家事託付張去為,身子託付王繼先。紹興和議前,有禦史彈劾王繼先與秦檜,宋高宗力挺道:“秦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有了這把保護傘,他更無所忌憚,“中外之士莫敢議者三十年”。
其四,權臣擅朝。
自宋徽宗後,宋朝逐漸轉向內在。南宋四大權相,秦檜另作別論,其他三人終成不可撼動之勢,都與皇帝的疾病密不可分。宋寧宗材質迂癡,膠柱鼓瑟地認定“臺諫者公論自出”,還自詡這是“法祖宗”。他認識不到,臺諫如受操縱,公朝執法也會淪為私門吠犬。韓侂胄掂出他的斤兩,在與趙汝愚的黨爭中,“首借臺諫以鉗制上下”,對他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宋寧宗不識賢愚,莫辨正邪,支持韓黨,打擊趙汝愚、朱熹等正直的士大夫群體,放任韓侂胄一手鍛鑄了慶元黨禁。宋寧宗如此資質,卻還經常繞過決策程式,內出御筆,亂下指揮,其後不久,御筆也落為韓侂胄的囊中之物。憑藉著私用臺諫與假借御筆,韓侂胄順暢地走通了權臣之路。
其後,韓侂胄草率北伐,終致大敗,朝臣史彌遠與內廷楊皇后聯手誅韓。宋寧宗不僅沒有抓住契機,收回權柄,反而“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硬是以自己的駑鈍無能目送史彌遠再坐權相的交椅。在韓與史先後專權的三十年裏,他對權臣唯唯諾諾,對朝政無所可否,“大臣進擬,不過畫可”。可以斷言,“南宋滅亡的種種症狀,早在宋寧宗後期就基本具備了”(拙著《宋光宗宋寧宗》)。
宋理宗晚年,賈似道雖已崛起,但未成權相之勢。度宗即位後,為抬高身價,要脅朝廷,賈似道一邊撂下挑子返回故里,一邊教唆親信謊報蒙古大軍南下。宋度宗弱智低能,大驚失色,親筆草詔,懇請他回朝主政,將軍國大事一股腦兒交其處分。賈似道入朝,度宗不顧人君之尊,竟向其答拜,還呼其“師相”以示尊崇。其後,賈似道一再故伎重演而屢試不爽,度宗甚至哭泣流涕,下拜挽留,權相之位終於不可動搖。權相賈似道與愚君宋度宗的關係,完全是韓侂胄、史彌遠與宋寧宗關係的升級版。
其五,傳承危局。
家天下是君主制的本質,世襲制則是確保家天下的前提。然而,至高無上的皇位,自君主制形成以來,始終是各種力量逐鹿問鼎的禁臠。宋代汲取了前代教訓,確立了祖宗家法,有效防範大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各種勢力的專權獨裁。然而,前文已述,在皇帝纏綿病榻時,祖宗家法往往形同虛設。而皇帝病危淹滯之際,由於君主自身原因,加上權臣與女後的干預,也會催生皇位危機。
君權的巨大誘惑,讓宋代多位皇帝即便痼疾纏身,依舊死不放手。宋英宗直到病重失語時,對請立皇子的臣下奏議,仍然老大不快。彌留之際,重臣韓琦遞上紙筆,請“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這才寫下“立大王為皇太子”。韓琦請他親筆注明名字,他吃力添加了“潁王頊”三字。唯恐變生不測,韓琦提醒趙頊“朝夕勿離上左右”,皇位這才順利傳給了宋神宗趙頊。
宋哲宗晚年夙屙不起,他明明沒有兒子,卻始終不立儲君。撒手人寰後,向太后聽政斷事,確定在神宗諸子中遴選新君。她否定了宰相章惇先後提出的兩個人選,認為端王最合適,章惇以為端王輕佻,不宜君天下。太后強調先帝就是讓他繼位,究竟是哲宗遺言,還是她自作主張,也就不得而知。於是端王繼位,他就是將北宋王朝推向靖康之變的宋徽宗。
紹熙末年,宋光宗的精神病越發厲害,宰相奏請立儲,他先是斥罵“儲位一建,就會取代我”,繼而禦批“曆事歲久,念欲退閑”,卻不表態究竟立儲,還是禪位,令宰執無所適從。太上皇駕崩,他拒絕出主大喪,政局變亂迫在眉睫。萬不得已,在太皇太后吳氏(宋高宗皇后)贊同下,才擁立了宋寧宗。為了遮醜,還將這次皇位傳承危機標榜成“紹熙內禪”。
在位君主宿疾在身仍不立儲,自然容易伏下傳位危機,但即便預立了儲君,在老皇帝淹病滯疾之際,皇位之爭仍會在內廷外朝暗流湧動。宋太宗在高梁河之戰中箭染疾年年必發,至道元年(995)更見嚴重,為防諸子日後爭位,便冊立第三子趙元侃為皇太子。兩年後,太宗病危,李皇后打算謀立其長子趙元佐(即前文論及的精神病患者),宦官王繼恩與外朝參知政事李昌齡、翰林學士胡旦結成了擁立趙元佐的聯盟,有意隔開皇太子與宋太宗。重臣呂端入宮探疾,見太子不在,便密派親信讓他即刻進宮。太宗撒手,李皇后主張“立嗣以長,順理成章”,呂端反駁道:“先帝立太子,正為今天。豈容另有異議!”在呂端的堅持下,奉皇太子登位,他就是宋真宗。
宋神宗病篤,其同母弟雍王趙顥有覬覦皇位的跡象,與異母弟曹王趙頵經常出入宮禁,甚至要求留宿大內。神宗“疾不能言,但怒目之而已”。宰相王珪、蔡確與朝臣邢恕也與二王暗通聲氣。宋神宗憂慮長子年僅十歲,擔心身後“皇位須得長君繼為之”,儘管打算自立皇太子,卻已說不出話,寫不成文。臨死前四天,宰執在病榻前奏立其長子為皇太子(即宋哲宗),他只能“聞言首肯泣下”。這才使奪位之戰大局砥定。
北宋重臣恪守祖宗家法,多次化解了皇位危機。及至南宋,權相替代重臣,傳承危局在中後期一再重現。而宋寧宗病危之際,權相史彌遠李代桃僵,最讓人扼腕歎息。宋寧宗膝下無子,晚年立太祖十世孫趙竑為皇子,自以為就算完成了國本大計。他的昏昧在於,分不清皇子與皇太子的根本區別:皇太子是唯一的皇位繼承人,而皇子不是唯一的,未必就是當然的儲君。得知趙竑不滿自己專斷朝政,史彌遠別有用心提議為寧宗已故堂弟沂王立嗣,推薦了太祖另一位十世孫貴誠。眼看宋寧宗病得危在旦夕,史彌遠矯詔改立貴誠同為皇子,賜名趙昀,讓他的地位與趙竑在伯仲之間。然後,一邊宣召趙昀入宮,一邊脅迫寧宗楊皇后配合其廢立。安排停當,這才宣趙竑上朝,聽預先炮製的“遺詔”,宣佈趙昀即皇帝位,他就是宋理宗。史彌遠從此完全拿捏住新君,繼續做穩他的權相,繼而趙竑遭迫害致死,南宋歷史進一步跌入了深淵。
史彌遠利用宋寧宗智力駑駘,出於一己的權欲,將其玩弄於股掌之間,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偷樑換柱,變易儲君。就皇帝疾病影響政局而言,這也許是兩宋史上最怵目驚心的案例,而凸顯的卻是君主專制與生俱來的制度弊病。這一先天弊病的癥結在於,既然君主專制的歷史命運最終取決於君主一人,當這“在予一人”沉屙不起,王朝的前途就可能岌岌乎危哉!
四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裏,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倘以現代政治學而論,“政治問責給制度的適應性變遷提供了一個和平的路徑”。然而,在他看來,“在王朝階段,中國的政治體系始終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即‘壞皇帝’的問題”(轉引自劉瑜《重新帶回國家》,2014年7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對他的“壞皇帝”概念,不妨作廣義的理解,即既指政治品質,也指治國才能,當然,還指本文重點討論的健康狀況。他以為,中國政治傳統始終是“國家能力過強”而“政治問責不足”。結合中國史上的君主政體來說,也就意味著皇帝所代表的君權掌控著超強的國家能力,但對其政治問責機制卻明顯薄弱。平心而論,在王朝階段,宋朝的問責機制也許堪稱完善。但這種相對完善的問責機制畢竟受制於君主專制政體,一旦出現了“壞皇帝”,問責機制也往往一籌莫展。
仍舉宋光宗為例,他以精神病患者君臨天下,危象頻生,亂局已成,朝臣葉適建議宰相留正“播告”皇帝病狀,免得“臣下輕議君父”,留正回答:“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禦朝自如,茲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這番話揭示了君主專制荒謬絕倫的那一側面:有病的“壞皇帝”倘若諱疾忌醫,而且感覺良好,自以為是沒病的“好皇帝”;人臣也就絕無說出“皇帝有病”的道理,惟有共演一出中國版的“皇帝的新衣”。葉適問責宰相,蘊含了宋代制度的合理成分;但留正不敢也不可能最終徹底問責“壞皇帝”,卻代表了君主專制下最真實的臣民心態,這種心態正是專制政體的必然產物。歸根結底,之所以會出現有病的“壞皇帝”,癥結就在於,集世襲制與終身制於一體的君主專制本身就是一個有病的體制,是應該被歷史淘汰的壞體制。
《皇帝病》提及一個概念,即“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207頁)。這一制度,說到底,就是對上級長官而不是對下屬百姓負責,對皇帝而不是對全體國民負責。在這種體制下,百姓與國民也就只能寄希望於皇帝與長官,期盼他們既英明又健康。
即便君主專制已從歷史前臺退隱,民主制度沛然成為時代主流,但國家領導人的身體健康與精神狀況仍然事關國家權力的正常運作,依舊是現代公民關注的大事。《病夫治國》指出:“對國家領導人身體和精神狀況的研究不再只是一種好奇心,一種公民或哲學利益的表現,這一研究成為所有公民的合法自衛問題。”所謂“所有公民的合法自衛”,就是指他們對領導人應該擁有其健康知情權,以徹底杜絕“病夫治國”現象的重演與失控。惟其如此,該書作者提出了“健康監督”的命題:“在執政過程中所應該實行的健康監督乃是議會監督的正常發展,目的是盡可能地避免民主制度的混亂及其向專制形式或多或少的偏離”,對公民來說,“經常顯得不足的政治報導應該由健康報導來補充”。
作者:虞雲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