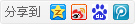虞美人·枕上
1921年
《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的词作。这首词写于1921年(有争议),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翌年春夏间毛泽东外出考察,此词写的是新婚初别的愁绪。枕上,取首句中语词,表明写枕上思念之情、乍别失眠之苦。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注释】
晓:拂晓,天快亮的时候。
离人: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1920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一说指罗一秀,作者的第一任妻子。
残月:拂晓时形状如钩的月亮。唐代白居易《客中月》诗:“晓随残月行,夕与新月宿。” 宋代柳永《雨霖铃》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代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
【译文】
我躺在枕上,成堆而来的愁闷让我愁成了什么样子?离别的愁绪,就像江海里翻涌的波浪一样难以平静。黑夜正长,天色总是很难亮起来,寂寞无奈之下,我只好起床披上衣服,独自坐到屋外去数天上的寒星。
等拂晓来临的时候,我的万般思念都已化成了灰烬,身边仿佛只剩有妻子的影子仍在陪伴着我。抬头望见一钩残月正在向西边沉落,面对此情此景,我不抛洒眼泪也没有理由!
【词牌格律】
中平中仄平平仄(韵),
中仄平平仄(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平平(韵)。
中平中仄平平仄(韵),
中仄平平仄(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平平(韵)。
注:标“中”字处可平可仄。
【赏析】
这首词写于1921年,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翌年春夏间毛泽东外出考察,此词写的是新婚初别的愁绪。枕上,取首句中语词,表明写枕上思念之情、乍别失眠之苦。
上阕写惜别之愁。一个“堆”字,形象地表现了愁闷之多;一句“愁何状”的设问,自然引出“江海翻波浪”。以流水与离愁关合,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方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化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都是借东流之水来比喻绵绵不断的愁思。这里诗人推陈出新,“江海翻波浪”以形象的比喻、强烈的夸张,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可谓是写愁的又一经典。如果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一比较,本句在状形、摹声、绘色方面,则更突出、更鲜明地写出“愁状”。诗人因愁闷而失眠,更感长夜难明,于是只好披衣起坐,仰望夜色苍穹,寂寞无奈中查数夜空中的寒星。那夜空中的“寒星”正像是离人的眼睛。这里,景与情完美融合,充分显示出诗人寂寞孤独的情怀。在毛泽东的手迹上此句原为“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后改作“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遣词造境上的改动,使此句的意蕴和色调更深更浓更富感染力。
下阕抒伤别之苦。开头两句,直抒胸臆,一个“晓”字点出是彻夜未眠;一个“影”字写出若即若离的别样之苦,“烬”与“剩”的鲜明对比写出伤别的深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捱到破晓,百念俱毁,只有离人的影像浮现眼前,拂也拂不去,唤又唤不来,令人十分的伤痛和无奈。望月思友,见月怀人,明月最能牵动离愁别绪。“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写出了柳永的寂寞无奈,而诗人遥对着西流的一钩残月,此时的情状和心情可想而知,以至两行酸泪汹涌倾斜出来,这是诗人不停的在心中涌动的无法抑制的情感的波涛。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读者至此,也会同样受其感染。
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2]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两首涉及对杨开慧的情感,一是《虞美人 枕上》,一是《蝶恋花 答李淑一》,一写于革命成功之前,一作于革命成功之后;一是诉燕尔新婚的离别之苦,一是叙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两词对照而读,使人感怀至深,潸然泪下。
赏析2
几句话就活画出一个杨开慧,她深爱着毛泽东,支持他的事业,但和别的年轻女人一样,她也矛盾、善感、容易误会、爱哭。
对于《虞美人·枕上》这首词,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把词中的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这样的定位,既非知人论世,也不了解词在文体上的特点。词是一种微妙的文体,长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不像诗那样更多地反映外部世界。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而词所表现的内心世界,并不局限作者自己。如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的主人公,“有人楼上愁”的那个人,到底是一个身在旅途的游子,还是一个颙望中的思妇,真是难说得很。
词体产生于歌筵,和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多是交给女子唱的,所以唐五代词一开始,天然走一条婉约的道路。闺情,春怨,孤独的女性的心情,就成了词的传统题材。温庭筠如此,花间派也如此。豪放词是词体的另类。毛泽东长于词体,他的自白是:“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这首词就属于婉约词。
这首词的内容是异地相思,从传统题材的角度看是一首闺情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枕上”这个题目就是很强的暗示。当然,写“枕”不必是女性题材,男性也可以这样写,如“枕戈待旦”。但这里写的不是枕戈待旦,而是离愁。“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两句一起就是对离愁的感性显现。“堆来枕上”这个说法,直接令人联想到头发,尤其是长发。用长发状愁,李白有“白发三千丈”之名句,那是只见头发不见人的。长发堆在枕上,就可以形容为“江海翻波浪”。在近代,只有女子才有这样的长发。用感性显现的手法抒情,是晚唐温庭筠开创的一种词风。毛泽东这首词也沿袭了这种词风。当然,“江海翻波浪”还可有别的解释,那就是比喻心情的不平静。心情不平静,自然不能安睡。“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长恨歌》“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虞美人》本为唐教坊曲,由霸王别姬的故事得名。曲调本来就是凄苦的,这个曲调以李后主所作“春花秋月何时了”一词最为着名。选这个曲调用来写夫妻的相思离别,是很恰当的。杨开慧很喜欢这首词,曾把这首词的词稿让好友李淑一看过。三十六年过去,李淑一还不能忘怀。1957年1月,她把自己怀念丈夫柳直荀烈士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寄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把《虞美人·枕上》这首词抄给她。毛泽东复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致李淑一》)于是,另作了一首《蝶恋花·游仙》“我失骄杨君失柳”为赠。毛泽东为什么说这首词“不好”呢?原因有二:一是婉约词本非他的长项,同样的题材,古今婉约词佳作多多,这首词好得到哪儿去呢。另一个原因,就是“晓来百念都灰尽”这样的句子,容易遭到误解,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特别不愿意披露。不过,毛泽东还是记起了这首词的全文,并抄下来,还对原来的词句作了一些润色(如将“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改为“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可见他在内心还是很难割舍这首词的。到1961年的某一天,毛泽东将这首词的抄件,送给一位名叫张仙朋的卫士,说:“这个由你保存吧。”毛泽东到底也是人,不是神啊。他一面说这首词“不好”,一面又心中藏之。不但心中藏之,还把它抄出来交给了一位可托死生的警卫战士,不让它随时间的流逝而湮灭,用心真是良苦。 (周啸天)
【历年版本】
这首 《虞美人·枕上》 ,最早发表于毛泽东逝世十三年后的一九八九年的《湖南广播电视报》。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此词写作于1921年毫无问题,因为原稿附有日期。
【相关争议】
一、重述发表时的故事
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正是党内“左”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刻。几乎就在《诗刊》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同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他着重考虑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外的矛盾问题。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 “阳谋”也开始出笼,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便在全国展开。那时,他发表的诗词,大都是“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和抒发革命胜利喜悦之情的“政治抒情诗”,尽是黄钟大吕,“铜琶铁板”之作。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一九五七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事情是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引起的。曾经在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早在红军时期就英勇牺牲了。他的夫人李淑一是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在读过毛氏这些大气磅礴的诗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她想起了一九三二年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起了昔年在开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九五八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氏似有两层深意。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白无误地说了一句: “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语,又几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尤其是权威的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那首”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党魁,毛泽东的生活是神秘的。而作为诗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后来却是尽人皆知。他不仅喜欢李白,喜欢苏轼、陆游、稼轩诸家,也爱读李贺,李商隐,李清照……好事者每称主席喜欢“三李”,真是将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简单化了。即使所谓“三李”,长吉与李商隐和李白的诗风,也是迥然不同的。其实,感情丰富的诗人毛泽东对诗歌爱好的广博,是远远超过权威注家们的想象的。他不仅对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佳句击节称好,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听到一首题为《吻》的新诗受到非议时,还以惯有的幽默去打抱不平,说:《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看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的心灵深处,也是和常人一样充满着浪漫情调的。儿女情长,何尝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据此似可断定,他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绝不是因为这首词涉及了他和开慧的个人感情,而不愿书赠李淑一,或由此而公诸于众。
到了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已经八十高龄了。不知是因为怀旧,“夜来忽梦少年事”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竟然在“文革”形势最混乱、最严峻的时候,却又意外地将这首《虞美人·枕上》连同那首《贺新郎·别友》一起,凭记忆写下来,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这些事,当时外人是一无所知的。这首词,在他老人家辞世以前,仍是云遮雾障,难窥全豹。
直到毛泽东逝世十三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湖南广播电视报》才将这首词透露出来。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恁。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说此词是赠开慧之作,大约起于此际。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两稿相较,除了下阕的“剩有离人影”一句的修改外,其它如“无奈披衣”与“寂寞披衣”;“皆”与“都”两处的改动,并无太大差别。重要的倒是确定了此词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后来正式编入《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就是此稿。我们研读此词,当然应以正式发表的文本为准。至于几处改动的“编校”和确定写作年份的过程,倒可略而不计。
二、“开慧所述”便是赠开慧的吗?
毛泽东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句话怎么理解?看来,编校者是拿它作为“赠开慧”的根据。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将这句话作为这首词是赠予开慧的根据,是很值得怀疑的。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这首词不像《贺新郎·别友》那样,当年连开慧都无缘一见(参见拙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载《书屋》二OO一年第二期)。开慧当年在看到或珍藏这首《虞美人》词时,和同在福湘女中读书的女友“述”些什么,我们当然无从寻觅了。大概她当时很受感动,至少是觉得毛润之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儿,因此才和闺中好友述说此词,并让女友分享她的感受与激动。数十年后,毛泽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在热恋中或新婚后写下的这首词,有什么 “不好”呢?他为什么婉拒了李淑一的这一请求,另作新词相赠?既然“不好”,为什么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又如此郑重地将它抄写下来,交给身边的人保存呢?
为什么?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写于“一九二一年”。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一九二O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在整个一九二一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这一年毛泽东一直以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为依托,向他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冲刺。从元旦那天新民学会集会,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共同目标开始,毛泽东就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行动,为建立湖南的共产主义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头脑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从家庭的角度讲,父母均已去世,这一年他回韶山过春节时,作为长子,他已经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弟妹都跟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让给人家住,田地典给人家种,债务一次还清,债权一笔勾销—他已经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生活上呢,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特别是心仪已久爱慕莫名的开慧,已经成了他的妻,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一个那留在记忆中韶山南岸上屋场七弯八拐的“老家”所无法相比的新家。应该说,他心底里满盈盈的幸福感,恐怕是他二十八岁年华中的珠峰。而杨开慧呢,自从她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心爱的毛润之后,她就走进了心灵的天国。他的理想就是她的理想,他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她一面读书,一面帮助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和新民学会开展工作。他和她这一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实、幸福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
不错,这一年,毛泽东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毛泽东年谱》载,一是二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六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十二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六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八月中旬才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诸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年近而立。作为那一个时代造就的精英群体中的杰出的代表,毛氏在思想上的成熟,也是走在同辈人前列的。这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自从一九一八年北京之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之后,他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随后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湖南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洗礼。曾经在他的思想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逐渐淡化了。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渐渐淡漠,模糊。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已经自觉地在为自己的信仰奋斗,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试问,一九二一年,除了上述不足挂齿的婚后小别外,还有什么事能让二十八岁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有什么事能让他“晓来百念都灰烬”?又有什么事情能叫他“不抛眼泪也无由”?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一九一九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 挽易昌陶》,写于一九一五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一九一八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 “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对有着养育之恩、自己无限尊敬的亡母,他说的是“必秉悃忱,则效不违”;对即将远赴异邦的同学,他说的是“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对早逝的挚友,他说的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幛,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成年(比如二十岁吧)以后的毛泽东,似乎真的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垮下来擎得起”的坚强性格。从他走进社会之门起,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何曾见过他有过哪怕是一瞬间的“万念俱灰”?更何况是新婚小别呢。
开慧大概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一九二一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年”的毛泽东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三、实事求是的解读——答客难
下面记录的,是彭明道和一位挚友讨论此词时的一段真实的对话。
客曰:你说,你是“实事求是”地解读,请试言之。
彭答:要论述一件事物“是什么”,首先最好搞清它“不是什么”。我已经论述了两点:不是赠开慧之作;不是作于一九二一年。
客曰:毛泽东的手稿摆在那里,他老人家写的明明白白是“一九二一年”啊。
彭答:美国有个哲学家说过,“记忆有时是会骗人的”。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份手稿,是他一九七三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着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作者按:此手稿见河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九九一年版,臧克家主编;新华出版社的画册《毛泽东》,一九九三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后来大概发现确实是错了,故此后这份手稿在各种出版物中,通过技术手段将这几个字去掉了)。
客曰:还有“充足理由”吗?
彭答: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一九一五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着字,似乎稚嫩得多。整首词的意境,率真,直白,作者的愁苦悲痛的情绪,一览无余。这与作者一九一五年(成年)以后的诗词,以及他晚年的诗论,相去甚远。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一九一五年。但毛氏一九一五年以前的诗作,现在有些出版物中收入的如“孩儿立志出乡关”、“独坐池塘如虎踞”等几首,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考证,均为他人之作,而少年毛泽东只略改其中一句,用以明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非他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这首《虞美人·枕上》,才真正是毛泽东的早期诗作。
客曰:早到什么时候呢?
彭答:他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即一九一O年春夏之间。
客曰:尔越说越玄矣!一九一O年以前,毛氏就有相思之作?
彭答:如果将《虞美人·枕上》视为单纯的“相思之作”,恐怕有“简单化”之嫌。这应是大悲大痛,大愁大惑之作才对。
客曰:一九一O年,毛泽东十七岁,何来你说的“四大”?
彭答:所以,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作点比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作者的面前有一位女“友”,作者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二是对方的神情,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月的“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作者自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眼”。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的真正含义,是无法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流泪了。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一九二一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客曰:你似将“不是什么”的道理占尽。能否就“是什么”言之?
彭答:这首词,恐怕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写这首词的时候,罗氏大概刚去世不久。所以,与其说《虞美人·枕上》是“相思之作”,倒不如说它是“自哀之作”更为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