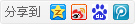京沪天地(一)
2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 “三豪杰” 。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后来同萧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
“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 ”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 “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 ,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 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 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旬,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看出自己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 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 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另外,可能还有杨开慧小姐的牵挂。毛泽东在拜访杨教授的宅第时和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小姐,杨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做工。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悠久历史、壮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占据。
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自己谦虚而矜持的解释来说明他不去马赛的理由: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这一决定是他已经形成的态度之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倾向。
与此同期。在120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人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据西方先进国家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列宁主义则与此不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国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列宁这样认为),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
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严谨的德国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境遇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泽东也颇为合适。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
他回忆说:
“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