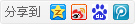1920(5)
11月7日—9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说本社“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并通告文化书社经售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及《新青年》等出版物二百一十二种。
11月中旬 致信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章程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这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
11月19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短文,指出女子同男子应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为女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呼吁。11月21日 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3日 因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二十五日,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林支宇任湖南省长。
11月下旬 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查游览。去萍乡期间,分别复信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
11月25日 复信旅居法国的向警予。说一年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音绝少”。自治问题发生时,空气至为黯淡。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以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明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日 复信在法国的欧阳泽,谈新民学会问题。认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讨论会务,一致主张新民学会的进行应采取“潜在的态度”。“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同日 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说: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张湖南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信中谈到自修问题说:“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
同日 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答复五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九日两封来信。说: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根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11月26日 给在法国的罗学瓒连复两信。信中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信中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时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自己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中国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体弱的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信中还反对“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倡导自由恋爱,主张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实践“废婚姻”。
11月 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为易礼容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写按语。按语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对于陈赞周所谓“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的看法,按语也不同意。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进行这种运动,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按语在谈到根本改造的计划时,提到并肯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11月间 应陈独秀函约〔1〕,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1〕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同月 致信萧三,说:“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11月30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同时编定付印。毛泽东在为出版通信集而写的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说明发刊的目的是,“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
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1〕,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蔡和森等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
12月2日 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
12月3日 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对过去有人诬控他双十节游行在省议会扯旗,这次又有人诬控他图谋捣毁省议会两事,进行辩诬。说“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12月中旬 复信张文亮,说: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十六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1〕。
〔1〕这时,长沙青年团已有二十多人。原准备陈独秀来湘再开成立会,因陈独秀赴广州,不能来长沙,遂于次年一月十三日召开成立会。
12月19日 在省教育会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影响办师范的,不仅是办法问题,还有不明白办师范重要的问题。“湘潭要教育普及,照现在造就师资办法,再过千年,还无希望。宜以此种情形先事鼓吹,造成舆论。”
12月22日 参加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为解决教育经费而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发言主张教育自决,说罢课还是消极,要准备积极的办法,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教育界应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实行自决自救,军费、政费都可以借款,教育是百年大计,也可以借款自救。
12月27日 给张文亮送去《共产党》月刊九本。
12月29日 同姜济寰、王季范、熊瑾玎、易礼容等在长沙县署出席文化书社议事会临时会,讨论文化书社“另觅社址”和“添筹股本”两问题。
冬 同杨开慧结婚〔1〕。
〔1〕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到她同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