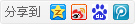1920(3)
4月1日、4日 两次致信留法的萧子升,并寄送平民通信社稿件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信中说,“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
4月上旬 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这时,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搜刮政策。张敬尧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1〕
〔1〕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着;《社会主义史》,柯卡普着。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罗章龙在一九九○年三月曾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4月11日 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5月8日 同新民学会会员萧三、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的陈赞周等六位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送别会。送别会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议决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为: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送别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中间“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5月11日 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岸。
5月 应彭璜之邀,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在上海民厚南里租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一个月后,彭璜写信给湖南的岳僧说,经过“考查北京已成各团的现状,调查社会生活的现实,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现在竟不能说不失败”!
6月7日 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信中强调自学和博学,写道:“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对于“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信中还说,旅京湖南学会,是一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在谈到自己的性格时,信中说:“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6月9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欺人太甚,有些难忍”。“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
6月11日 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十二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十四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十七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文章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文章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合起来便可得到全国的总解决。“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6月18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6月23日 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二十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向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的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信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申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
6月30日 致信罗章龙,告以在上海的见闻。信中谈到要将湖南的事情办好,搞自决自治。罗章龙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复信说:“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
6月 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2〕
〔1〕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关于此事,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有一段回忆,她说:一九六三年毛主席突然提出“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必定派秘书送两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满累计两万元。主席还说: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